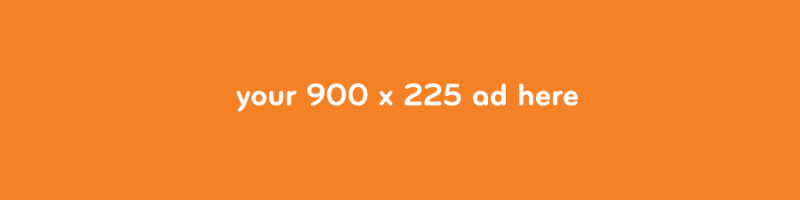同往年一样,女儿又不在家。陈莉和吴建军去蒲江旅游,石象湖、朝阳湖,一处处逛过去,熙来攘往的人潮中,喧嚣声一浪一浪打过来,眼睛和耳朵都被填满,但心里依旧感觉少了点什么。
2007年1月,那个料峭的隆冬,刚满18岁不久的兰兰远渡重洋,赴美留学。母亲陈莉看着她瘦小的背影像小船一样义无反顾起航,消失在安检口,心里涌动着“海一般广袤的悲哀”。夫妻俩当时憧憬着,“等女儿学成归来就好啰”。不曾料到,2013年,兰兰突然告诉父母,自己将在美国登记结婚。
冰与火的冲突就此开始。任凭陈莉和先生坚决反对,最终都败给了女儿的义无反顾,一如18岁离家时那般,她只留给父母一个决绝的背影……
出国
她劝女儿,“你爸也是为你好,你一个女孩子,独身出去那么远,他不放心。”
2005年,兰兰念高二,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末,晚餐饭桌上,兰兰一言不发垂着头,一双筷子在碗里探来探去,这在活泼开朗的她是鲜见的。
陈莉刚想开口问,兰兰忽然抬起头,望了望她,又望了望父亲吴建军,嗫嚅地说,自己要出国读书。空气瞬间凝固,饭厅里充溢着窒息的沉默。
“啪”,父亲把筷子拍在桌上,盯了女儿两秒,坚定地表达了态度——“不行!”
兰兰不认,气汹汹地反问为什么?吴建军并未解释,重复了一遍,“不行。”
“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就不行?”兰兰望着父亲铁青的脸,掷下碗筷跑回房间。一扇门重重关上。
十二年后,当时情景如在昨日。吴建军说,自己当初坚决反对,主要是觉得女儿的想法来得太陡然,让他一时无法接受。“我认为女孩子还是留在身边好,即便要出去,也要晚些时候。现在这样年轻,一人独身在外,很难令人放心。”
母亲陈莉也舍不得女儿出去,但她夹在中间,总不能放任父女俩赌气,私下里两方劝慰。她劝女儿,“你爸也是为你好,你一个女孩子,独身出去那么远,他不放心”;转过头,她又劝先生,“女儿长大了,有主见了,再说出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很好嘛?之前老李儿子出国,你不也赞成?”
吴建军当然清楚,孩子出国读书,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可以领略不同的文化,增长更多的阅历和见识。可事情发生在别家孩子身上,道理就分外分明。一到自己的孩子,就被千丝万缕的感情绊住。
“要不等大学毕业再出去?”两口子想办法留住兰兰,提出谈判条件,但兰兰一点让步的意思也没有。陈莉与先生互相望望,一声叹息。陈莉只好开始送兰兰做出国前的语言培训。白天学校课程繁重,兰兰只有夜里抽空看单词,练习题,两口子看电视不敢开大声音,走路都踮脚。好几次,陈莉在凌晨还见兰兰房间门缝漏出朦胧的灯光。心疼女儿的她很想冲进门抓起女儿的手说:“咱不去了,行吗!”终于还是无奈转身。
后来,兰兰托福考了600多分的高分,顺利拿到留学签证,还申请到奖学金。但看着女儿的这些成绩和荣誉,陈莉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心里五味杂陈——她知道,女儿离家的时间,就快到了。
离别
当女儿瘦弱的背影在泪眼迷蒙中彻底消失,她身体一软,“就像脊椎骨被抽掉了。”
帮女儿收拾行李时,陈莉总疑心有东西忘了带。兰兰被母亲搞得有些不耐烦,“妈,到了那边,啥都可以买”。但陈莉仍然一遍遍梳理行李清单,一件件物品往行李箱里塞。陈莉一边收,一边抹眼泪,同时提醒自己要提前练习好告别,在机场可不能这样绷不住。
练习最终还是失败了。在安检口,看到兰兰头也不回地挥手,陈莉的眼泪颗颗滚落。当女儿瘦弱的背影在泪眼迷蒙中彻底消失,她身体一软,靠在先生身上,“就像脊椎骨被抽掉了。”
航班是1月7日下午的,行程有些辗转:先从成都出发,再到香港(专题)转机,等到了威斯康星州已是第二天零点。兰兰提前了10来天去,麦迪逊大学还未开学,因此校方无法安排接机。
其实,兰兰早就在网上联系了网友,可陈莉始终不放心,“从小到大,她连一次远门都没独自出过,况且是出国?”再联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在成都的家里,陈莉自己把自己吓得神经衰弱。她不停在丈夫耳边唠叨。先生劝她少安勿躁,但说归这么说,其实夫妻俩心里都放不下,“终日惶惶”。
她周而复始地问先生:“你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网友靠谱吗?兰兰长这么大,可是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呀。”陈莉心里也清楚,她的这些问题,先生没法给出什么行之有效的安慰,但她还是不断发问。“当时我需要的,也许只是焦虑本身,有心可操,心里不会太空荡荡”。
遥远的女儿
那时,越洋交流基本靠国际长途。到了约定那天,她整天都会满心雀跃,可电话一接通,她有很多话想问,但每次都忍住了:“我怕女儿烦。”
整整一周后,女儿的电话终于姗姗而来。那时没有微信,手机与网络也欠发达,越洋交流基本靠国际长途。彼此听着对方经过电磁波转换后略微扭曲的声音,想象对方现在的模样。
陈莉忍不住责备女儿为何这时候才来电话,刚数落了几句,就听到女儿说这几天“蚁居在一间十平米的角楼里,门没锁,楼下还有黑人”。她立即中止了责怪,心有余悸地开始“复读”:睡觉要用凳子把门抵住,不要单独跟陌生人相处……
2007年4月16日,震惊世界的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专题)惨案发生。陈莉买菜时听人说起,“妈呀,发生在美国”,还没听清具体是哪里,就撒腿跑回家,急急忙忙给女儿打电话,偏巧没接通。她担心得要命,心都快跳了出来,每隔两分钟就打一次女儿电话,并四处求助其他中国留学生(专题),后来终于知道,兰兰到图书馆温书去了。
女儿随后复电,听到母亲快要急疯,自己也又急又气,反复向母亲解释:“妈,我是在威斯康星州,(跟枪击案发生地)根本不是一个地方。”确认了女儿安全,陈莉总算安下心。晚风穿过客厅,背心凉津津的,陈莉一摸,衣服背面全汗湿了。
陈莉笑起来:都说我神经质了,其实我还算好的啰。她的好朋友黄阿姨,每天早晚都给国外读书的孩子打电话,一遇到不接,就开始电话轰炸,给舍友打,给老师打,甚至打到大使馆,“不确认孩子平安,电话就不会停”。
为确定女儿的安全,陈莉跟兰兰约定:至少每3天与家里联系一次。到了约定那天,陈莉整天都会满心雀跃,可电话一接通,聊的不过是“吃了么,吃的什么,睡了么,早点休息”一类温吞寡淡的话。她当然有很多话想要问,但每次都忍住了:“女儿具体的生活,我不是不想了解,但那些事在电话里说起来太啰嗦含糊,我怕她烦。”
空心的时光
以前难以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孤独,开始慢慢有了形态——陈莉的孤独,是开门关门时巨大的声响,是电视里兀自播放的节目。
除了对大洋彼岸的牵挂,难挨的还有夫妻俩在成都的生活。在空间上,陈莉跟女儿隔开几万里;在心里,感觉就像是隔了五年十年。“以前整个身心都扑在孩子身上,现在孩子离开了,简直不知道做什么好。”
工作时还好,在办公室,有人声儿,有事儿做,时间很容易消磨。独处时最难挨,房子空荡,静寂,“兰兰以前活泼多动,在家叽叽喳喳的,她一走,整个家就静下来……”陈莉侧躺在沙发上,把电视打开,调大音量,有时不小心睡着了,梦里依稀出现女儿的身影,半夜醒来,电视还在沙沙播着。有时候她会坐在床头看报,报纸上的每个字都认识,看过却不知到底讲了什么,只是枯坐。
以前难以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孤独,开始慢慢有了形态——陈莉的孤独,是开门关门时巨大的声响,是报纸上呆头呆脑的方块字,是电视里兀自播放的节目。
这样百无聊赖过了一阵,陈莉尝试找点事儿做,之前送女儿培训时加了几个QQ群,群里都是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大家一起参加英语班、合唱团、舞蹈团,结伴打发子女不在身边的寂寞时光。
初来乍到时,陈莉和几个年轻母亲聊各自儿女,她发现寂寞的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一位刘阿姨说儿子离开的头一个月,自己彻夜彻夜地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得靠吃药入睡。她先生工作又忙,经常出差,自己一个人在家。为了抵御这样的空寂,她把收音机、电视机从睁眼开到闭眼,还特意花了几千块买了条善解人意的小狗,就为家里有点声音。还有一位樊阿姨,在孩子出国确认不会回来以后,重新生了二胎。“确实太寂寞,养花养草,养猫养狗,说丢就丢了,但再有个孩子,还是不一样。”
大家说着说着,不禁都带着点哭腔。几位稍年长的留学生父母靠近来,劝大家看开些:“孩子并非父母的‘私有财产’,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和自由。孩子走了,舍不得很正常,但我们也该有自己的生活。”在春节、中秋这些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群里经常组织晚会活动。比如今年中秋前夕,留学生母亲们便穿上漂亮的纱白长裙,换上古典的团花旗袍,聚在一起,唱歌、朗诵,热热闹闹。
可这热闹的保质期有限。陈莉在旁边的小房子里,听着外边满屋子的歌声,谈笑声,碰杯声,眼里有种空茫。“亲情血缘这些东西,我们这代人终究割舍不下。外面再热闹,最后还是要散伙回家……只能安慰自己,忍忍吧,孩子回来就好了。每次一这样想,心里就会踏实很多。”
妈,我要在美国结婚了
“我们听了很惊讶,自然不会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她远在万里之外,能拿她怎样?”
2011年,兰兰毕业了,并成功进入美国一家知名房产公司。朋友邻居都称赞:你家兰兰能干哦。可吴建军和陈莉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夫妻俩轮番上阵,试图劝女儿回来,“成都也有房产公司嘛?在哪儿不是工作,回来不一样?”兰兰却理直气壮地说,“说回就回,这工作得来有多不易,你们哪里知道?”
“那我和你妈就容易嘛!”吴建军忍不住大声责骂,气得剧烈咳嗽,陈莉一面拍着他的后背,一面安慰来日方长,“算了,先由着她,等她混不走,自己就回来了。”劝完先生,自己却忍不住哭得更厉害。
工作的事情还没谈拢,紧接着,夫妻俩便收到更坏的消息,兰兰说自己准备在美国登记结婚了。“我们听了很惊讶,自然不会同意,她在那边结了婚,就定了根,还能回来吗?”陈莉叹了口气,眉头微扭。“但不同意也没办法,她远在万里之外,能拿她怎样?”
兰兰邀请父母去美国见证她的幸福时刻。吴建军和陈莉都拒绝了:“心里都要气死了,哪有心情来参加你的婚礼”。但过了些时日,夫妻俩又忍不住往美国打电话:你们抽个时间,还是回成都补办个婚礼。
照片中的女婿,终于站到了自己面前。男孩的家乡在台湾(专题)岛,说话温文尔雅,勉强可以听懂吴建军夫妻俩口音浓重的川普,这令两口子稍微宽心。陈莉又开始笑:“合唱团里曾阿姨的女婿,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来成都)大家打了招呼之后,都直直地坐着,不知道说什么。”
小两口带回来各色礼物,给吴建军买了衣服、香烟,给陈莉带了包包、项链。夫妻俩穿戴着出去散步,邻里看见了,直夸他们好福气,“女儿女婿有出息哟!”多听几遍,陈莉自己也恍惚觉着不错,女儿女婿在美国知名地产公司与金融机构上班,收入体面,自己和先生有空就和朋友出去旅游,潇潇洒洒,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对啊,还有什么不满足呢,陈莉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可心里为啥还是空呢,就是那种让人不安心的空,空得难受”。
父母的纠结
陈莉心里清楚,外人看来的美满,于自己而言,完全就是一团无法理顺的乱麻。这团乱麻的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解开——
现在倒是就这样过了,可未来呢?我跟她爸爸老了怎么办?
叫她们回来,她们肯么?她不敢想。
那过去和孩子一起生活?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又该如何生活呢?
去美国?
她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案例。陈莉朋友张阿姨的儿媳,前年在美国生了孩子,老两口乐呵呵过去照料,但因为不懂英文,连婴儿食品,都要儿子把说明书翻译好了才晓得用餐分量。
张阿姨的先生老陈是典型的四川人,无辣不欢,而美国的食物,冷、酸、甜,吃了几个月,老陈天天嚷着要回四川。后来考取美国驾照后,老陈开车去买菜,兴致盎然预备做中式大餐,结果却在高速上下错出口。手机偏巧没电,路上又没个人影儿,没法问路。好容易碰见人,语言却不通,所幸老陈记得大概的住家位置,他学着外国人说中文的腔调把地名说出来。路人虽未听懂,却从老陈一张焦急的脸上大致读出了他当下的处境,将手机递给他。老陈终于辗转联系到儿子。
经过这次教训,老陈几乎不再出门,看着一群窗外谈笑风生的外国老人,与妻子相顾无言。最终,这样坐牢般“与世隔绝”的日子,老陈实在过不下去,住了半年不到就坚决回了成都,任凭儿子再怎样劝也不妥协。
坐在自家的露台上,老陈一脸笑容:一回成都,啊呀,整个人都觉着舒坦,浑身轻松,所有毛病都没了。
回成都?
去年冬天,老陈走路摔在冷硬的鹅卵石地上,在床上躺了半年,张阿姨特地飞回来照顾,儿子也回来看了一趟。老陈拉着他的手,满怀期望地说:不如你们回来吧。
小陈避开不看父亲的眼睛,不知该怎么回答。妻儿、房产、事业都深深扎根在对岸,难道要连根拔起,跨越整个大洋移植回来?这些年含辛茹苦拼下的基业,就这样白白放弃?
“好好休息”,他留下一笔钱,一句话,匆匆飞走了。老陈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气得大骂,“薄情寡义”。
这些身边事,陈莉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如果女儿叫我去(美国),我应该不会拒绝。”但那边到底是个浑然陌生的环境,一切都是未知数,她想了想,改口道:“要不然呢,就只有美国成都各待半年吧。”至于先生的意愿,她迟疑半晌,“应该会去吧……”
聊天暂停在成都深秋微凉的空气里,她摆摆手,又捂住了脸:唉,这些问题,我们还没认真考虑过。到底怎么办,真没一个完美的答案。
有时,夫妻俩从电视或报纸上看到一些老无所依的惨闻,像独居老人倒在客厅死后一周才被发现,陈莉说,每次看到这些事儿都一阵胆寒,只能很快换台或者关掉新闻页面。
深陷在沙发里的身体重新坐直,她把手机递过来:你看这个新闻,教育部今年3月做了一个留学生相关调查,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如同自我安慰一般,她算起了账:50多万家庭,理论上就有50多万对父母,100多万人呢。像我们夫妻俩这样的情况,应该不在少数吧。到时如果谁家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我们就照着人家(那样去)解决。
陈莉关掉手机屏幕,身体重新陷入沙发里:我们有时候也会反省,是不是我们太传统了,把团圆看得太重了,为什么就不能两代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呢?但她很快又反驳自己:团圆当然很重要,何况我们就这一个女儿,把孩子留在身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