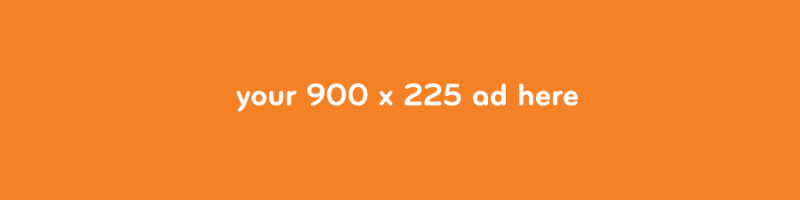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09年第10期总第323期
原标题为《北回归线上的疤痕》,有删改。
作者|周宇
这是篇刊于中越战争30周年的文章,采访了当年参战的双方老兵。当年他们都是芳华正茂的年轻人,战争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虽不为他们所理解,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2009年3月11日,昆明的一家皮具美容店,52岁的店主赵永刚,坐在满屋的皮鞋、油漆和皮衣中间已忙碌一整天。
一个和赵永刚年纪相仿的人径直步入店内,与他商量晚上聚会的事情。这个人告诉赵,聚会有老首长出席。赵永刚开始为难起来,他想见见昔日的首长和战友,但又舍不得丢下这满屋的鞋子。
赵永刚是中越战争退役老兵,二等功臣。2009年2月17日,是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日,2月份以来,赵和战友的聚会、扫墓和纪念活动也因此不断。

1986年8月,“这个成都来的女娃,在里面呆了快6个钟头了,还独自在墓地徘徊……”麻栗坡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说:“她好像在仔细读着每一块烈士的碑文……”这位来自成都的女子叫崔佳,她说:“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让他们太孤独……”
3月6日,越南北部老街省老街市,50岁的摩的司机阮文贵又拉到了一个中国客人,这个客人的目的地是城外的老街省老兵公墓。1万越南盾,阮文贵很高兴能做成这笔生意,并且不介意在客人参观公墓时,在公墓门口等候。
公墓位于老街城外约3公里,在通往老街市开发区的路上,周围少有人家。公墓里空无一人,只有少数墓碑前有蜡烛或是香火的痕迹。公墓正中的纪念碑上写着“祖国记功”,纪念碑前只有一个花圈,上书“祖国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这里埋葬着一些在中越战争中的越南阵亡者,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
时近三八妇女节,老街街头到处都是卖花的摊位,根据习俗,很多人都会买花送给家中的女性。但在公墓里,一束花也看不到。
见客人对中越战争有兴趣,阮文贵介绍,自己就是那场战争的老兵。阮脱下外套,卷起袖子,他的右臂上赫然呈现一个炮弹弹片留下的伤痕。
在老街市,许多开摩的的司机都和阮一样是中越战争中的越南老兵,他们并非老街本地人,是因为战争而留在了这里。
在2月17日那天,越南河江省境内的1509陵园,同样鲜有来访者,整个陵园只能看到一两束鲜花。一个越南老兵点燃了香,孤独地纪念他埋葬在这里的上千名战友。
中越战争是中越两国最近的一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战争。据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称,中国有2万人阵亡,伤6万余人。中国方面,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从1979年2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中国士兵赵永刚、越南士兵阮文贵和他们各自的战友,在红河岸边展开厮杀。每个人身边都有大量战友倒下,每个人都见证了城镇的毁灭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战争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虽不为他们所理解,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1986年10月13日,一位基层指挥员大吼一声仰脖干了酒,瞪大眼睛举着酒杯说:“我第一次喝茅台,竟是壮行酒!”
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中越士兵的各自命运
1979年2月17日零时,22岁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接到命令,乘坐橡皮艇从河口县暗渡红河,进入越南的黄连山省(现分为安沛省和老街省)。
当时赵永刚头脑一片空白,感觉像在做梦。两年前入伍时,赵完全没想到会打仗。对他来说,部队只是个跳板,为的是退伍后可以进工厂。
1978年下半年,军区首长突然密集地视察,一位首长还在视察之后丢下一句话:“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赵隐约感到,“立新功”可能意味着要打仗了。

年底,对越作战的任务下达。士兵们被告知,中越两国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南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不但大规模排华,侵略柬埔寨,还炮击、骚扰祖国的南疆。
赵永刚在暗渡的时候,20岁的阮文贵,这个在驻老街的越南地方部队中服役的士兵,还在睡梦中。阮文贵与赵永刚同一年入伍。高中毕业后,阮文贵没考上大学,按国家规定进人民军服役3年。
阮文贵的中学时代是在中越友好的宣传中度过的,他在高中学习了3年中文,这是当时越南中学教授的唯一外语。在学校,阮被告知中国给了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他从未听到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
在高中毕业之后,阮发现了变化:许多中学不再教授汉语,而是改教俄语。阮对此感到不安。阮原本是准备训练后被派往柬埔寨战场的,但最终留在了老街。
凌晨2时,暗渡成功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摸到越军阵地,对方喊口令,他们抬枪便打,不久,赵听见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炮声。
赵永刚当面的越军,当时大部分正在阵地背后一个砖瓦厂的院子里看苏联电影,对战争爆发毫无准备。顺利占领越军阵地后,赵永刚发现,阵地上的重机枪和用来对付步兵的高射机枪都没用上,阵地前的陷阱里甚至没来得及插入致命的竹签。
两小时后,河口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强渡红河。一个叫谢明的通信兵看着身边的战友一波一波地乘坐橡皮艇,高喊“同志们,为保卫祖国领土,冲啊!”,奋力向河对岸划去。对岸越军则对着口号声的方向猛烈射击。
约一小时后,中国炮兵开始压制越军阵地,炮火映红了夜空。中国军队终于抢滩渡河成功。
清晨,谢明渡过被中国军队鲜血染红的红河后,才发现自己配属的连队突然少了很多人。很快,大批陌生的面孔填充了刚刚空缺出的位置。
正准备起床洗漱的越南士兵阮文贵被中国军队总攻的震天的枪炮声吓坏了。此前,阮文贵和他的战友每天都在担心中国可能的进攻。此后的日子里,阮只知道到处都是中国的炮弹,到处都是源源不断进攻的中国军队。阮与所在的部队边打边撤。

在逃到老街南面约20公里的地方,阮的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他身边的战友一批批阵亡,尸体被活着的人遗弃。阮文贵被弹片击中了手臂,但侥幸冲出包围圈。不到一个月,阮文贵所在约100人的连队就阵亡了49人。阮的一个兄弟战斗单位则全部阵亡。
赵永刚所在的尖刀排在进入越南4天后遭到重创:被埋伏的越军前后堵在了一片山谷之中,激战中,一名机枪手死在了赵的怀里。赵所在的连队,在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包括抬走的伤员、牺牲者、被打散的人,160余人损失了100人。赵因勇敢荣立二等功。
谢明所在部队损失更大。“每一分钟都在死人”,谢回忆,即使在已被攻占的城市也是如此。谢被子弹击中了腹部。来到柑塘的第三天,谢明和战友们平时喝水的水塘里突然漂满了尸体。大家这才知道此前柑塘火车站发生过肉搏战,死去的军人都被丢进了水塘,在水底沉了2、3天后才浮了起来。
战地卫生员刘英记得,第一具战士的遗体被送进医院时候,院长手势轻柔地为这个年轻人擦拭血迹,还关照她们这些卫生员,清理的动作要轻,擦干净后,要用棉纱填充好烈士的鼻孔、耳孔,最后换上新军装。这个程序随着战事的惨烈迅速被打破。伤员和烈士越来越多,卫生员们再也没有时间清理遗体,只能把他们装进黑色塑料袋,用绳子扎紧。
令刘英难忘的一天,两辆罩着绿色大篷的军用卡车开进医院,车上跳下个军官,大叫着“快包包我的战友”。刘英抓着车厢板往上跳,一眼瞥见车厢里挤满了被烧得发黑的遗体。一个还有口气的战士,夹在奇形怪状的尸间大喊“妈妈啊”,她吓得手一松,跌坐在地上,止不住地抖。
战争中的性启蒙:
看见越南女兵的裸体
对谢明来说,与死亡一样印象深刻的,是在战火中对女性身体的最初记忆。1978年10月,他才18岁,热血沸腾,放弃了就读昆明师范学院的机会,应征入伍。
他和他的战友大都没有见识过女人,战场上敌方大量的女兵,让他们充满了好奇和幻想。但他们看到的女兵,一直都只是尸体。
一次战斗中,谢的部队碰到一群在山头上似乎打光了子弹的越南女兵。她们全部赤裸着上身,只穿短裤,雪白的乳房清晰可见。战友们呆了,端着枪跳出战壕围了上去,枪响了,那些跳出战壕的小伙子全部被射杀。
狂怒的士兵们边冲边射击,用刺刀捅死尚在挣扎中的越南女兵。谢明记得,他那一刀捅在了一个越南女兵的臀部上。

1979年3月14日,谢明所在部队占领重镇柑塘。在离柑塘2公里的一个农场,谢明又一次见识了越南女兵。她们被包围在一个牛棚里,用树枝挑起一个白色的胸罩当白旗,来回摇晃。小伙子们再一次沉不住气,想看看活着的越南女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隐藏在牛棚里的机枪猛烈开火,10来个年轻士兵应声倒下。
牛棚最终被火焰喷射器摧毁,清理战场时,在里面找到29个越南女兵的尸体。
因为通信兵的职责所在,谢明两次都幸运地没有冲过去。
柑塘驻扎期间,通信团的几个女兵去市中心一排带洗澡间的公寓洗澡。谢明觉得不安全,劝阻失败后,便持枪在外警戒。刺耳的炮弹声从空中划过,3发炮弹击中谢明身后的公寓,将其夷为平地。
炮击过后,谢明扒开废墟,10名女战友全被埋在洗澡间里。
残酷的现实是,不是每个年轻的战士都能在战后娶到倾心的姑娘。卫生员刘英记得,部队撤回时,她给几十名中方战俘做过身体检查,这些战俘随后提前复员回老家。她知道有些人回家后,长久地受到地方民众的歧视,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

战争结束很久后,谢明去过中越贸易口岸河口县城,越南籍“小姐”随处可见,最低仅需20~30元,这令他震惊。谢明了解到,她们当中的一些人,父辈在当年的战火中丧生或致残,此后陷入贫困并得不到足够教育。这令谢明难以平静。
“兄弟之间”的战争
很多年之后,阮文贵说服自己,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与抗美、抗法战争完全不同,“亲兄弟还打架呢!”
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赵永刚也觉得自己对待越南人,应该像在国内作战对待老百姓一样。
2月17日上午,赵永刚第一次见到逃难的越南老百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惊恐的老年妇女和孩子,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呆在家里不要乱跑,并分给爱抽烟的老年妇女们烟抽。
赵有时会问村民:“中国好不好?毛主席好不好?解放军好不好?”得到的答案都是“好”。一些村民在解放军进村时就翻出早年的毛主席像,挂在家里。
一次包围越南村庄,并成功抓获大批战俘后,赵所在营经过请示上级,决定向村民们宣传中越友好。赵永刚所在连队手持冲锋枪包围了一块水田,其他连队则跳进田里,为越南村民插了两个小时的秧。
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上来,一些村民的脸上带着笑容。赵永刚觉得那是“皮笑肉不笑”,大家都知道这是表演。
谢明所在部队也曾试图建立与越南村民的“友好”。战争初期,谢的战友们被命令见到逃难的越南老弱病残,要背回来予以救治。但难民们并不领情,一些战友被背在背上的“难民”突然拔刀捅死。
血的教训让谢明和他的战友只能放弃友好。

1986年5月3日,中国士兵针对越军惯用的战术特点,对阵地前沿的越军屯兵洞实施搜剿破袭。
谢明在越南乡村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包括捷克的摩托车、苏联的康拜因、法国的装卸车、日本的收录机。
在进入越南人家中搜查时,谢突然发现桌子上一个疑似定时炸弹的电子装置,战友们立即卧倒,但炸弹并未爆炸。一名战友壮着胆子按了一下按钮,“定时炸弹”开始播放音乐。此后谢明才知道,这原来是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而法国的装卸车则被误认为是新式坦克,被士兵们用火箭弹摧毁。
1979年3月28日,谢明的部队在柑塘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谢明的部队撤退时,同时完成炸毁当地主要建筑物的任务。柑塘政府大楼、百货大楼、老街市政府大楼、发电厂等建筑,以及一个磷矿、大批桥梁被全部炸毁。谢明记得,老街城里那些法式的漂亮小洋楼也都被炸毁,一些藏有武器或民兵的村舍则直接用燃烧弹烧毁。
阮文贵突然听到中国人撤退的消息时,感到比战争的爆发更加难以理解。30年后,阮依然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直被往南方赶的部队开始追在撤退的中国军队身后打。阮跟着部队打回老街,一直打到了红河岸边。
阮文贵看到的老街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兄弟之情荡然无存,越南士兵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立即杀死。那时候,阮一见到红河对岸清晰可见的中国人,就恨得咬牙切齿。
战火十年国境线
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阮文贵和赵永刚都在一年后退役。两年后,双方争夺重点集中在广西境内的法卡山、云南麻栗坡县境内的老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等地。北回归线以南不远的中越国境线上,再次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

麻栗坡县烈士陵园的《老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概况》(下称《概况》)称:“自一九七九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越南当局本性不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重警告,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西侵柬埔寨,北犯我国边疆,先后派兵侵占了我国云南边境老山和扣林山地区十个高地。”
1981年5月、1984年4月,双方在此地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内地的各大军区轮番上阵,与越军厮杀。《概况》称,仅其中一次长达100天的战斗,中国军队就攻克了50多个高地。
战火在这一西南边陲小县燃烧了整整10年,距今天麻栗坡县中越天保口岸30公里的老山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战场。
959名解放军和支前民兵阵亡者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其他一些则被火化后运回原籍安葬。陵园中的阵亡者来自19个省市,最小的年仅16岁,他们当中有的阵亡时入伍仅3个月。

1986年10月14日,突击队长马全斌率部强攻越军占领的阵地之后,向指挥部报告。有人说,马全斌惶恐的表情有损军人的形象。血肉横飞的激战中,马全斌也是血肉之躯,并非刀枪不入,“惶恐”的瞬间正是人性的真实写照。
天保口岸不远处盘龙河畔的一个桥头曾经是遗体转运站,村民们记得,整卡车的遗体被堆放在这里,再转运走。当地的老太太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死去的年轻人,以及满地的遗书和遗物,一起跪在路边痛哭。
越军同样死伤惨重。据云南省边防部队记载,仅在1984年4、5月间连续100个昼夜的激战中,就击毙越军副团长以下官兵数千名。
一名越南汽车兵对越南记者回忆,早上载着满车的士兵上前线,晚上拉着满车的伤员和阵亡者回来。满车的伤员和尸体之间,一段香蕉树的树干上插着点着的香。汽车兵原本以为会有一些伤员能活下来,但在到达目的地后,经常发现一车人里只有他自己是活的。
在越南河江省临近中国一侧,遍布着众多烈士陵园。仅在渭川县烈士陵园,就埋葬着1600名死于中越战争的军人。
国境线两侧的公墓
1980年,赵永刚退伍后,被安排在昆明市活塞厂上班。此后的30年间,赵几乎每年都要去屏边县的烈士陵园,为团里的46位烈士扫墓。
赵每月从50余元工资中单独拿出5元,作为扫墓的路费。等凑够了大约一个月工资,赵就会请假,然后踏上去蒙自的火车,再转蒙自到屏边的汽车。第三天早上,赵就可以看到陵园里的战友们了。

赵在战友们的坟前点燃一支烟,洒上一杯酒,或是放个苹果,一边哭一边和他们说话。扫墓令赵沉浸在为国捐躯的荣耀感之中。数年之后,这种荣耀感逐渐褪去,赵永刚和战友们说的心里话也越来越多。
“大哥,我今天来扫墓,心里难过。我们打仗,保卫江山,到底为了什么?”赵对着墓碑说。年复一年,赵永刚在扫墓时唠叨着自己对退伍兵待遇太低、社会不公、腐败的不满。但赵永刚从不在墓园里提起的是,这场战争正在被遗忘,他怕战友们听了伤心。
2月至4月间,总会有越来越多特殊客人抵达中越边境,他们是来祭奠埋葬于此地的亲人和战友,追忆和纪念一段人生重要经历。一年中零散前来凭祥扫墓的老兵和家属,更难以计数。

再为烈士播放一曲邓丽君。邓丽君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她演唱的流行歌曲深受当时年轻人的喜爱。女子的着装、双喇叭录音机、祭奠的小物品,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典型象征。近旁是刘东沛烈士之墓。刘被追记一等功,追认为中共党员。
国境线另一侧的越南,同样有大量的烈士陵园,在谅山市郊的谅山省越南人民军烈士陵园,其气派程度不亚于凭祥的南山和匠止陵园。这个陵园中间高耸着纪念碑,上书“祖国、记功”,这里安葬的450余名越南军人几乎都死于1979年二三月份,还有部分在1980年代的边境战斗中阵亡。
这个烈士陵园,是该省“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常有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组织扫墓活动。
并非所有的阵亡将士都能在陵园里安息。时至今日,依然有人不时发现散落在中越交界山区的两国军人遗骨。
1991年,一位中国边民曾在越南一侧见到2名越南军人的白骨。军人死在废弃的军事工事旁边,工事里面的钢筋已被人拆走卖掉,白骨却依然躺在那里。
这位中国边民点了3支香烟插在他们面前,聊以慰藉。
200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对赵永刚和谢明都很重要。越战老兵,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此前的数天里,两人所在部队老兵分别聚会予以纪念。
谢明参加了他所在部队砚山籍战友在县城的聚会。他是砚山籍186名战友中唯一的一名军官。这场聚会最终只有约30名战友到场。一些农村战友出不起来县城的路费,另一些到场的农村战友,还穿着当年打仗时的解放鞋。
但这一天对阮文贵并不重要。越南的军人纪念日是7月27日,这一天,参加过抗法、抗日、抗美、中越战争等历次战争的越南军人都会庆祝。历次战争中,中越战争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阮从来不去老街城边3公里的军人公墓扫墓,因为许多战友的尸体早已不知去向。偶尔,阮也会思念死去的战友,这令他又回忆起对中国人的仇恨。只是面对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和忙着去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阮轻描淡写的仇恨显得无处安放。

1986年7月20日,老山前线某师侦察连的战士刚返回阵地,顾不得摘去身上的子弹袋,和着只能听到节奏却听不到旋律的音乐,吼着叫着就跳起了老山迪斯科。
并非每一个越南老兵都能轻易放下当年的战争。
前述河江省汽车兵就在2月17日来到公墓祭奠死去的战友。汽车兵给每人点了一支香。30年前,这里是打得最火热的地方之一,但在现在,烈士们静静地躺着。汽车兵说,山顶太冷了,希望2月17日能有人来给死去的战友们点香,让他们温暖一些。
阮文贵不愿意去的老街省公墓,赵永刚反而去看过。去红河对岸的越南看看,是众多中国老兵的心愿。
2005年,赵永刚和老战友们去屏边扫墓。对长眠在屏边的战友们一番倾诉之后,活着的战友们决定去老街看看。因为赵没带身份证,两名越南人民军士兵帮助他们偷渡了过去,中国老兵们为此每人支付了60元人民币。
赵想去老街省的军人公墓看看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越南军人,这样心里会稍稍好受一点。不过走到公墓门口,赵没敢进去,他怕自己的年龄引起公墓管理者的猜疑。但赵不知道,这座公墓里面并没有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