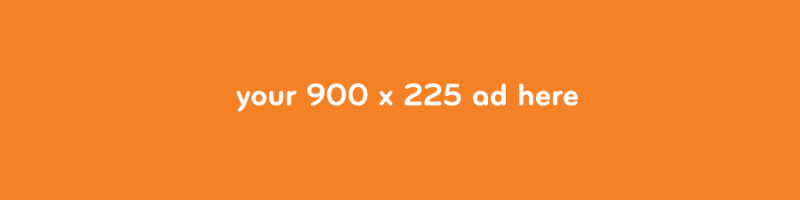说起来,应该是2018年7月份的事,大致应该是最早被美方取消签证的上海学者之一。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从美国开完一个学术研讨会回国,然后接到了国土安全部的电子邮件,说是电子入境审核状态更新了;接着就是收到了美国上海总领馆的邮件,要召回我的护照;通过校外办交上去之后,过了两天发回,在十年签证上盖了“取消(Revoked)”章。
其实在这件事发生前,大概也有点心理准备,毕竟这不是第一次与美国个别机构打交道,算起来也已经有那么3-4次的“遭遇”了。
第一次是2015年去美国开中美互联网论坛会议,在西雅图()入境,全团约10人,我当时拿着因公护照跟团由外交通道正常过海关,却被一名警察单独叫到机场“小黑屋”问话,他们问了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叫什么”“从哪来”“去哪里”“平时在哪工作”“工作具体内容是什么”“薪水如何”“谁发工资”,折腾了大概30分钟,这应该是第一次打交道。
那次会议结束后,随团由旧金山()出境,我当时已经办完安检和出关手续,然后就有三名身穿“边境控制”制服的警察在安检后面通向登机口的路上等着我,直接要求搜走我的手机、手提电脑和随身行李,并要求我提供电子产品的开机密码,记得是一个白人两个华裔()的组合,两个华裔年长的香港()腔,年轻的似乎偏台湾()腔,检查过程中基本是年长的说,其他两个不说,不过显然站C位带队的是那个年轻白人。提供完他们要的开机密码后,我问,为什么要查?年长华裔说,你的签证有问题;我接着问,我这美国上海总领馆发的因公护照的签证有什么问题?那货似乎有点怒了,甩了一句,查出来以后会告诉你的,就跑了。
这时大概是登机前25分钟,然后,直到登机前5分钟时,他们将电脑、手机和随身行李还给我,后来开机发现原本电量100%的电脑,还回来后电池显示只剩百分之七八十,耗费将近25%的电量,很明显大概就是复制了一遍。虽说这是我私人的电脑,不过回来后我也不会再使用,又买了个新的。还给我的时候什么也没说,距离登机也只有5分钟,我本来还想追几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不过看着时间,也就算了。客观上来说,因公护照和签证都没有啥问题,前面那句话,不过是他憋出来的套话。
第二次也是去美国开会,这是第一次在美剧以外看到活的FBI人员,而且还接触了一下。当时是凌晨5点多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降落,迷迷糊糊从飞机上走下来,刚走出飞机廊桥时,忽然有两个人叫住我说“您是沈教授吗”, 我当时还纳闷,没听说主办方有接机啊?而且这地点似乎,也不太对。
接着,两人自报家门是FBI负责网络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部门的,问我这次来开会期间啥时有空,要邀请我一起喝杯咖啡。没办法,于是就在机场和这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他们的态度还算委婉,说了我的一些情况,以显示熟悉程度。既然对方这么熟悉,那我就很轻松的开始寒暄,顺口就把在旧金山被搜查的事情和他们聊了下。他们大概也有点意外于我的坦率和直接,就说了些类似“部门大了什么人都有”“有些人比较聪明,有些人就比较那什么”的话给搪塞过去了。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第一次被FBI人员请喝咖啡,拿了行李之后就地在机场喝了一杯卡布奇诺。
第三次就是2018年到美国开一个有关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中美俄三方研讨会。有意思的是,等会议召开的时候才知道,主办方邀请的所有俄罗斯学者全部被拒签,原本一场聚集中美俄三方学者讨论中美俄的会议,结果变成中美学者讨论中美俄。因为2018年中美关系的整体形势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去美国之前,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建设的。结果真的就遇上了,那天晚上七点多,我抵达入住酒店办理登记注册,刚办理完准备上电梯时,突然有两个人从电梯门前楼道的沙发上“蹦”起来问“您是沈教授吗”,然后又闪了闪自己的证件,说是FBI的,想请我一起吃顿饭聊聊。于是我把行李放进房间后,便回到楼下,在饭店的餐厅和这两个FBI人员边吃边聊。
显然,这两人和之前碰到的FBI还是有所区别的,之前两位上来就说明自己具体任职部门是负责网络安全的,但这次只说是FBI;总体氛围也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他们问我是否为中国政府工作,我当下反问,你们所谓的“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学者研究项目的经费基本都来自相关的政府资助,这些项目都是正常的学术研究项目,没啥特别的,相关信息也是公开的;如果这算为政府工作的话,那我确实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如果说是拿情报之类的事情,那当然就不是了。
问到一半时,得知消息后的会议主办方的一位美国教授走进来了,有点气冲冲的和那两个FBI的说了几句,FBI坚持说自己是例行公务,教授也在表达了不满后走了。因为是我多年的学术交流伙伴,所以后来我们私下吐槽了这种令人无奈的局面。
但无论如何,当时在我们很多中国学者看来,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确实超出预期。我们能感受到他的焦虑和不自信、周遭氛围有所变化,但没有料到变化会如此之快、影响会如此之大。
整体看,结合相关类似事件的数量和频率,可以说显示的就是美国的焦虑、不自信和脆弱,而这也正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一个重要征兆。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实力就此已经衰落或者立刻就要衰落,但至少美国人开始变得不自信了,他认为这区区两百多人,就可以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造成重大损害。这是非常可笑的。
这种不自信又会体现在他对自己这套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之上,这一点可以从班农这批人身上看出来。右翼白人始终认为,当前美国的政治体制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背离了他们的保守价值观。实际上,现在像班农这样的人,在所谓“应对当前委员会”等机构内,走的是一种将美国式的冷战与一定程度上的极右翼相结合的路线模式。
然而好玩的是,起初外界将班农这样的人视为特朗普政府内正在崛起的新兴政治人物,结果他很快就被抛弃和边缘化。为何这么厉害的人第一时间被从白宫里面踢出去?又为何取而代之的是博尔顿、蓬佩奥这批同样荒谬的右翼政客进入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政府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很多在班农这些人看来理所应当的事,比如立刻和中国干一架,资本家根本不会允许,因为对美国的收益会有很大影响。
过去美国对部分自然、科工领域的学者拒签,但这次延伸到社科领域,对人文学者“下手”,美国走到这个地步确实是外界没有想到的。目前来看,还不能确定、也难以判断影响范围会有多广。换而言之,无法确定今天的美国是不是已经判定像我们这样的学者去交流就已经足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者他对中国的认知已经愚蠢到以为对我们这样的学者施加压力就可以对中国产生某种实质性损害。这个举措本身就非常没有格调,它突显的是一种混杂了傲慢、焦虑和无知的情绪。
另外,美国除了对中国不断使出“小动作”外,还开始愈发明目张胆得把手伸进拉美等地,甚至公开喊出颠覆政权这样的话,然而事实上这些行为早已被证明根本行不通、也没有取得成功。这恰好体现了当下美国的三个问题:政策创新能力为零、兜里没钱、只能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做纯粹的负面性言语攻击。这正是美国衰落的典型象征。
本来美国去这些地方干涉是砸钱开道,但如今没钱。现在美国跑到拉美等地,警告那里的人不能跟中国混,对方当然就会问不跟着中国混跟着美国怎么混,你能给我什么好处?但美国的回答却是,跟着我混,就一定要让我赢、一定要让我获利,对方自然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美国的这种举动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体会到的是口惠而实不至。就好比说,你过来给我上一堂民主课,如果上完课后扔下来的钱够三年GDP,那就忍受让你说教,至少能赚钱;但现在我正欢快地赚钱,结果你过来跟我说STOP、这样赚钱是不对的,那我也只能反问,如果这钱我不赚了,那要去哪赚,跟着你走我有什么好处?结果你却告诉我,“跟着我走,赐予你被我剥削的荣耀。”
今天美国的困境是,资本主义金融进入金融垄断阶段之后,垄断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境。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加上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所带来的整体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此消彼长,美国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如果没有中国,那或许还能撑,因为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比烂。
再将视线拉回中国国内。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中国学者,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公知、美分、带路党”会视而不见。总体而言,普通网民对他们的偏好程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一些局部环节可能还会有反复,但就长期趋势看,他们在国内影响正在下降。
首先,归根结底是由中国自身发展所决定的。如果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得够好,那么他们就像蚍蜉撼树,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其次,确实和美国自身发展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带路党、公知、推墙派”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他们提前将自己绑定在美国站在正确历史的一边,中国是错误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如果到最后证明美国错了,那么他们就错了,或者说这个世界上不只一条道路,中国的道路也是对的,他们也会很尴尬。
现在初步证据呈现,到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曾经很得意地作出了聪明判断,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上从中国跳船从而和美国绑定;但这个选项有很大概率是错误的,这主要不是取决于美国的失误,更多的是中国做好了自己的事。而且,越往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越是国际交流多眼界开阔,所谓“公知”对他们能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来讲,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近年来,中国话语的崛起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理念,可能存在一些争议,但最要紧的仍是做好自己的事。这主要分三点,第一,不管叫什么名字,实际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跟随你做的国家获得了哪些收益,这是实体层面;自己没做好,美国衰落了,不代表自己会上去。第二,你做的这些事、让别人获得的收益,其内在规律是什么?是运气好、人品好还是有一套理论体系?能不能将其包装好,让大家能听懂也愿意相信,这是话语能力的问题。第三,要处理好关系,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把事情做好、把话讲清楚,还是非要别人说好话才认为这是对的?以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常态化现象,就是不管做得有多好、把话讲到什么程度,国外的主流媒体就是不承认,这该怎么办?就是“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让他们自己玩,慢慢地从多数变成少数、从有影响变成没影响。
一件事是否正确,是由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是否符合历史规律来判定的,正如中国话语正确与否并不是由西方社会认可与否来判定的。过去,我们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认知,好像中国的行为必须得到国际认可才是对的,这个判定本身就是不对的。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带一路”,当然,如果能表达得好一点,减少一些基于误会造成的批判,会发展得更好。如果做好了之后,还是有某些为批评而批评的,为颠覆而批评的,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批判可能正是我们要拥护的,要知道当年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很受欢迎,难道我们也要跟着这样作吗?
总而言之,首先,我们做了什么事、做好了没有;其次,这些好事好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说清楚让别人听懂看懂。只要做好这两件事,那些反复死咬着胡言乱语的人,也就无需理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