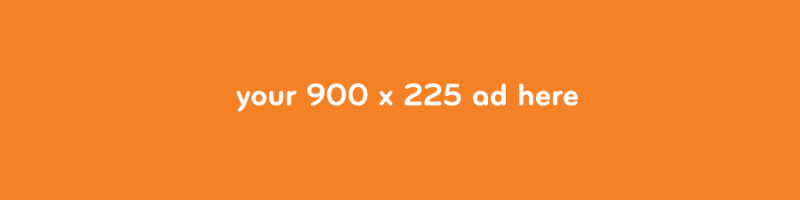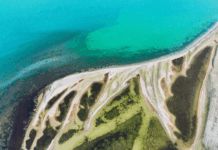资料图:特朗普。
近日,一档电视节目引发社会对中国男性青少年“阴柔化”趋向的忧虑。该节目试图以“小鲜肉”形象对中小学生展现亲和力,却引起社会特别是父母们的猛烈挞伐,斥之为“娘炮文化”。这种对“男子气概”的内在渴求实际上是男权主义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但父母显然又希望自己家的男孩能多一些“男子气概”。
这种男性“阴柔化”焦虑不是中国的孤立现象,而是一种全球化现象。有诸多社会学分析表明,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承平日久之后,竟也发生了“佛系化”,进入一种普遍低欲望的社会精神状态。欧美社会也出现了民主化与多元化社会规范下“男子气概”的边缘化,奇特的趋势呈现为:男人更像女人,而女人更像男人。与这种“男子气概”普遍赤字的趋势相应,女权主义及女性在政治与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日益上升。这引发了人们对世界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乃至于异化的普遍焦虑,尤其是来自男性世界权力旁落的焦虑。
性别政治问题伴随人类政治文明史。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存在男女护卫者问题。柏拉图从城邦主义的角度惊世骇俗地提出了男女平等及女护卫者的主张,表面来看是超前的女权主义代言人,但实际上女护卫者的角色规范及平等地位是按照男护卫者标准加以设计的。这种同质化已经无所谓男权和女权,但总体上仍然是“男子气概”的哲学肯定与制度化。因为理想国城邦中的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护卫者的男性标准气概有效维护了男性主义的权力秩序,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阳刚气质。但柏拉图似乎也意识到这种“阳刚护卫者”的衰变趋势,他通过城邦的败坏与政体的下坠来讨论政治演变问题。他对政治演变中欲望对理性的主权性征服保持高度警惕并设想全套的理想国建构方案加以反制。
与柏拉图相比,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同样对政治衰败与男性气质异化保持敏感,以其《君主论》和国家理性对抗“命运女神”的捉弄与征服。在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的哲学反抗背后,都隐藏着对“命运女神”之欲望性和无常性的深刻恐惧,其本质就是对“阳刚护卫者”或“君主”之权力秩序崩溃的恐惧,一种象征意义上“去势化”的恐惧。
总体上,西方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尤其是主权哲学的持续建构,就是对“男子气概”的哲学肯定以及对“命运女神”的持续反抗。为了这种反抗,西方哲学家造出了“利维坦”,造出了“骑士精神”,造出了“科学主义”,造出了“理性国家”。但这种理性哲学男性化的思想与制度建构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面临着非理性主义与解构主义的长久对峙,终于在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陷入精神性失败。
二战后的文化多元主义及政治正确价值观推崇的是一种“去国家化”的、隐含绝对和平主义的女性政治哲学取向,其终极形态就是默克尔式的仁慈的、人道的、圣母般的民主政治。这种泛女性化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人类对平等和多元化价值的过度消费,其后果就是对保守主义之整体价值与传统美德的解体。但其实西方民主价值观本身就内含着对整体主义和权力秩序的解构,其逻辑机理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就已道明:民主推崇一切趣味平等,承认一切差异和多元化,其结果必然是美德和秩序的崩溃,以及欲望的市场化及绝对合法化。当代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后现代化主义及全球化过程的拉平效应,切合的正是这种泛民主的价值观及其极致追求,而其代价就是普遍的美德崩溃与认同危机。这些,也都可以视为理性哲学的失败及命运女神之主权的确立。但这对于健康的民主政治及世界政治而言似乎并非福音。
于是,在最近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对“命运女神”的再次哲学反抗和政治反抗。在哲学上,有西方斯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有非西方文化中保守主义的普遍复兴。在政治上,世界似乎重回了“强人政治时代”。2016年特朗普当选,希拉里败选,这一选举事件不仅仅是美国的政党政治轮替问题,也是当代政治文化中的“男子气概”重建问题。特朗普主义带有“男子气概”中的理性、粗俗、直率和狡诈,刺破了多元主义政治文化带来的种种矫揉造作的阴郁气质氛围。特朗普与希拉里的选战辩论,以及特朗普与默克尔的欧美人权路线争论,具有男性强人反抗“命运女神”的特别隐喻及象征意义。
与之类似,俄罗斯的普京,日本的安倍,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都有着某种男性主义与克里斯玛(charisma)相混合的政治气质。这些强人领袖都有着明确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及战斗精神,甚至有着“帝国化”的想象和冲动。这些表现在多元主义民主价值规范中是不正确的,但却受到了长期被压抑和消声的“隐匿选民”的持续而强劲的支持。美国政治中,尽管特朗普丑闻不断,但建制派和媒体越批评,特朗普的民意支持越高。美国那些“去势化”的民众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久违的阳刚与直率,尽管可能只是表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但却满足了普通民众解脱自身无力感和疲软状态的美学移情。在政治感性分析中,特朗普的“强硬”就是美国“失势”男性的集体“雄起”。
这就造成了世界政治的“再男性化”,其影响是根本性的:其一,战争威胁的上升,即这种政治强权主义的男性诉求,需要通过战争加以洗礼,需要具体的征服事实加以抚慰,而这对于和平而言是一种精神反动和威胁;其二,宪法规范的弱化,即这些政治强人对所在国家既定宪法规范框架存在改造和突破的冲动,固然可能出现某些局部的制度创新,但带来的宪法波动与政治不稳定也是显著的;其三,全球化的逆转,即这些政治强人的基本思维是本国或想象帝国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二战以来全球化既有的规则体系与规范原则不是以守法伦理自我约束,而是以破坏者自居,世界秩序有重回二战前的下行趋势;其四,这种诉诸“再男性化”的政治哲学重建与政治风格再造未必取得最终的成功,因为二战以来的多元主义民主文化及人权全球化已经深入人心,依托相对稳健的宪制结构和公共文化,对这种男性主义的反向冲击具有持久的“驯化韧性”;其五,助长全球保守主义的回潮及其政治制度化,加快第三波“民主化”的全球逆转,整个全球治理陷入“公共性标准”的失范周期;其六,对这种失范与失序的政治与文化重构,东方文化与中国文明必须也应当做出独特的构成性贡献。
当然,这种“再男性化”的政治文化与世界治理的波动仍然是正常的历史周期现象,是规范与力量的周期性冲突和调适。某种规范主义的长期适用可能带来教条化和僵化,而依赖规范本身无从识别和克服危机,这时就需要某种事实性、存在性的力量打破既有规范。这种打破固然不可能取得根本的成功,但却引起了规范反思的深度展开,有助于建立一套新的、可容纳新生力量和异质诉求的整合性规范体系。当这种男性反抗及制度变革周期达至高潮而终结时,就是新一轮和平主义规范周期的开始。似乎最终总是“命运女神”的胜利,而“再男性化”不过是提供了反抗进步的契机与动力。
总之,中国身处这一大变革的世界格局之中,不可能独善其身。而积极理解、适应及抓取这一轮世界政治“再男性化”的制度变革与利益重组契机,是中国传统文明、民族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哲学奠基与制度更化的重大机遇和战略性抓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海外网专栏作者)
更多中国理论权威解读,尽在海外网—中国论坛网(www.china-theor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