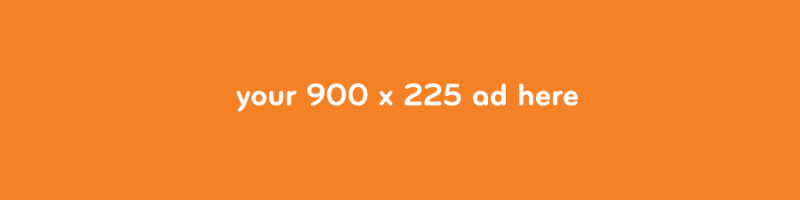作者: 坚强的橘子
患癌10年,一路披荆斩棘,也曾经绝望过,但现在的我却越来越坚信自己是无比幸运的。1个月前,美国医生告诉我:我体内已经检测不到癌细胞了。那天,我走出医院,站在波士顿的街道上,看着天空飘落的雪花,我有些恍惚,这十年来的风雪,我真的度过了,今后什么都不会再怕。
我是浙江的一个高中老师,35岁时,我被确诊为黑色素瘤晚期。10年前,国内还很少有黑色素瘤专门科室,网上也几乎查不到什么资料,我糊里糊涂地放疗、手术、化疗,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来到美国,不久,国内医生给我打来回访电话,他们想确认我是否还活着,那时我在国内治疗的病友全都离世了,只剩下我一个。
来到美国我才发现,癌症病人根本不应该过早放弃希望,在美国治疗的4年时间里,我开始变得坦然,在美国一代又一代的新药面前,我们只需要相信医生,并把所有的烦恼交给他们。因为只要多坚持一天,我们重生的机会就会又多一分。
黑色素瘤?!
2006年,我以为自己得了中耳炎,右耳不停的产生积液,当地医院也一直查不出所以然。从那时起,我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用针管抽掉耳朵里的积液,不然就听不见声音。但积液越来越多,我去医院也愈发频繁,从最初的两个月抽一次,变成了两周抽一次。我第一次怀疑,这是不是什么严重的病?
2008年初,我去了省医院,医生没有只帮我检查耳朵,也检查了我的鼻子。结果在鼻子里发现一块特别大的黑东西,已经从咽鼓管里冒出来,当时真的差点把我吓死。
省医院不敢给我做病理,我就去了北京的三甲医院,一家挂不上号,就再去另一家。最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活检病理结果是:咽鼓管咽口恶性黑色素瘤。
那时,我从没听说过黑色素瘤,也甚至没有明白“瘤”就是“癌症”。走出诊室时,我还有些懵,医生对我很好,很快帮我安排了放疗,来到放疗室,我才第一次明白什么是恐惧。
生不如死的治疗
放疗室里,一屋子的病人,脸上都开了花,我才知道放疗光线照到的皮肤会发黑,有人的脸甚至只能用皮开肉绽来形容。我当时才35岁,孩子还在上小学,要是我变成那样,日子一定过不下去了。
我不敢想,又别无他法,只好稀里糊涂地开始放疗,一个多月做了30多次。病友们的脸一个接一个地“开花”,我也越做越害怕,每做完一次放疗,我都要不停照镜子,最后我的脸居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软腭2度糜烂,病灶几乎没有缩小。
然而,当我去另一家三甲医院做PET-CT时,那个医生却说:“有你这么傻的人吗?应该先手术,再放疗。”在我刚开始觉得人生可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又一次陷入恐慌。
我的主治医生很快安排了微创手术,把那块黑乎乎的东西给切了。我记得手术那天正好是汶川地震,我的家人在手术室门外,看到走廊的灯都在摇晃,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但我真的活下来了,我至今真心感激这位主治医生。
不过,16天后,我要面对的是生不如死的化疗。
我的化疗药有5、6袋,还有一堆护肝、护肾的药,要从早上8点,一直输到晚上将近12点。
第1天,我还很自信地跟老公说:“化疗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会那么难受。”第2天,我就认输了,上吐下泻,胆汁都吐出来了,什么都止不住。第3天,我彻底崩溃了,那感觉我无法形容,只觉得那真不是人该受的罪。第5天,我开始发烧,烧到彻底不明白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1个化疗周期结束后,我回家休息了21天,在这21天里,我整个人都提不起来,只能软软地瘫在床上,吃不下饭,什么也做不了,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散落在枕头上。这感觉,我现在回忆仍然深有恐惧。
第2个周期开始后,我完全没有缓过来,我根本没有办法自己走进医院,必须要两个人搀着我,把我架进去。问了病友我才知道,让我有这么大副作用的药物是顺铂,我拼命哭着跟医生说:如果不换方案,把我折磨死的不是癌症,而是化疗。
更改方案后,停用了顺铂,我坚持做完了全部化疗。
复发
但好景不长,2012年11月,我的左耳开始出血,活检显示我的黑色素瘤复发了。接下来的经历,我现在回忆起来,还忍不住想哭。
病理出来后,主治医生建议我去别的医院做头部MRI和PET-CT确认。另一家医院的医生,拿着片子对我说:“没什么大问题。”我没有告诉他活检结果,只是问他:“能不能再仔细看看?”他说:“你这人有毛病啊?我说你没毛病!”
我告诉他活检结果后,他拉长声音说了一声“哦”,拿起一只红笔说:“这个地方好像出问题了。”我心里特别生气,因为那个亮点,那么大,我都能看见,他看不见吗?
后来,主治医生马上为我安排去见手术医生。
但是,第二天手术医生一见到我,可能是担心承担责任吧,他不想给我做手术,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原话:“你做手术有可能瘫痪,也可能面瘫,不管是什么,你的后半生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说得那么直接、冰冷、决绝,没有一点点避讳。这甚至让我的家人动摇,开始有人劝我放弃。我感到了一种从骨头里来的寒冷与孤独:人在这世界上能绝对依靠的,从来只有自己。
如果横竖都是一死,那我就是要去试一试!我剃光了头发,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开颅手术。术后第2天,我睁开眼睛,再次看到了这个混沌的世界。我要来镜子,没有面瘫,又动动胳膊和腿,都还能动。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我就是能这么活下来。
可是手术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术后复查发现我的病灶出现肺转移。主治医生说,国内没有好的治疗方案了,但你有BRAF突变,实在不行就试试美国的药吧,但是国内还没上市,你得自己想办法。
绝望之中,我开始四处打听主治医生所说的药物。通过某些渠道,我辗转买到了威罗菲尼,这是美国FDA在2011年获准的第2个治疗黑色素瘤的特效药。
那时,1瓶威罗菲尼要6万5,我1个月就要吃掉两瓶。再加上以前化疗、放疗的费用,为治这病我至少已经花了100万。
最后的希望在美国
于是,我开始想,既然在国内治疗花费也不少,为什么不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看一看呢?也许那里有我最后的希望。我对自己说,如果美国也没办法,我这一生,如此而已,无怨无悔。
去美国,是我之前一直没敢动的念头。语言不通怎么办?哪家医院比较好?到底要花多少钱?他们能否收治我这样的病人?就在我焦虑至极的时候,老公在网上查到了一家红杉投资的出国看病中介——盛诺一家,他们可以提供所有的服务,我真的非常庆幸自己及时找到了他们。
于是,我让他们帮我整理、翻译了病历,很快他们就帮我预约了一家美国在黑色素瘤诊治方面非常权威的哈佛附属医院。
到美国的第二天,他们的客服人员就陪我去见了美国医生,他是一位哈佛教授。走进医院,我看到大厅有人在弹钢琴,后来我还看到有人在弹竖琴,我才知道,他们是为了舒缓病人情绪的志愿者。

我来到黑色素瘤的专门科室,分诊台的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地问我:你今天怎么样?希望你今天过得开心。
他为我带上病人的手环,我来到候诊室,这里有很多沙发,没有一个患者和家属需要站着等待。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等待就诊,每个人都有事做,因为医院提供了免费的杂志、报纸、咖啡和零食,还可以借用iPad。我发现美国的医院,就像五星级酒店一样。
终于见到了首诊医生。一见面,这位金色头发的白人老头就站起来和我握手,问我来美国适应吗。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详细分析了我的病情,并回答了我整整三页纸的问题,这样的交谈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从他的眼神中,我读出了自信和坚定,这让焦虑不安的我一下特别放心。
美国医生说我可以继续服用威罗菲尼,没有必要化疗或者手术,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可能用上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耐药,到时他会帮我再调整。
用药1周后,医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一定要去医院。患癌6年,我从来没遇到过医生主动找病人的情况。
我坐在诊室里,医生走进来,他笑着问我:“你愿不愿意参加临床试验?这个试验的效果很可能优于你现在的治疗方案,而且药品免费,但你必须在美国先住一个月,以便我们观察。”
免费?!我当时整个人都懵掉了,感觉黑暗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光。几年来,我不断地想为什么偏偏病的是我?我做错了什么?我甚至早已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我要穿什么衣服。
原来,老天还是帮我的。
参加临床试验
进入临床试验后,我要每个月来美国检查一次。起初,我很担心试验药物有没有副作用,但还没等我开口问,医生就主动告诉了我:临床试验会有哪些风险、药物有可能的不良反应、如何应对等等……
医生的助手甚至把手机号告诉了我,如果我身体出现任何不适,都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这在国内几乎无法想像。
而且对于风险,美国医生也不是那种“恐吓”式的告知,他们总是很耐心、很人性化地向我解释,我不用在恐慌中做出任何迷茫的决定。
医院里还有花园。
当我对病情担心时,那位美国医生总是微笑着对我说:“这不是你应该操心的问题,你只需要放宽心,我一定对你负责。”我发现这是中美医生在理念上的最大差别:国内医生在尽力避免责任,美国医生敢于承担责任。
药物最初的副作用让我有些腿疼,腿上起了一些红疙瘩。用药一年多后,我的记忆力开始下降,脸也开始发麻、发黄,起了很多痘痘,但我就这样坚持了18个月,病灶从7毫米缩小到4毫米。
2015年10月,由于临床试验的药物产生了耐药,美国医生又帮我制定了另外一种治疗方案:使用最先进的免疫药物进行治疗。两种药物分别是:Yervoy (ipilimumab)和Opdivo (nivolumab),一共用了四个周期,大约3个月后,我转移到肺部的8毫米病灶,消失了!
和病友普及一下这两个药物的背景信息。Yervoy和Opdivo是美国最先进的免疫治疗药物,是目前公认的最可能彻底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法。现在这些药物都已经被美国药监局正式批准上市。
就在我开始进行免疫治疗后,我接到了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回访电话,他们想确认我是否还活着,那时我才知道,和我同期治疗的国内病友,已经全部离世。
是这些药让我活了下来。我不禁想,那些病友,如果也能用上这些药,他们的人生也许不会就此停摆。

战胜癌症
用药第1周,我就感觉头脑突然清醒了;第2周,我开始可以正常吃饭;第3周,痘痘全部消退了,皮肤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到了第4周,我感到了那种久违的神清气爽。我只需要定期到美国用药、复查。
用药后,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我回国照顾突然重病住院的母亲,没能休息好。再回到美国复查时,我直挺挺地晕了过去,幸亏身边有陪同人员,他及时送我去了急诊,不然,就那样晕在波士顿的大街上,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说到美国的急诊,真的是没法比。各科的主任大夫都来了,因为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我究竟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当时我的胳臂抬不起来、走不了路、还有中风迹象,主治医生、神经科、放疗科等等科室的医生来了5、6个,我躺在病床上,模模糊糊地看着他们忙前忙后,我真的一点也不害怕,这么多医生在帮我,我怕什么呢?
耐药后,医生又建议我参加Keytruda(Pembrolizumab)的临床试验,这个药物我一直用到现在。
医生将我用药的频率从3周1次,渐渐变成4周1次,这样我只需要每个月来一次美国。
2017年2月1日,我永远记着这个日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你的体内已经检测不出任何癌细胞,你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生活了。”
我真的战胜了癌症!
把绝望变成希望
那一天,我站在波士顿飘雪的街头,真不知道自己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真正最开心的时候,都是在美国的医院,见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天真的笑容,忽然之间我就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不算什么。
突然之间,我好像可以有更多的人生目标,敢去期待未来,也许我真的还能再活30年,以前我只敢盼着自己能见到儿子上大学,现在我敢期待着他结婚生子。
还记得,我在儿子读高中时告诉他,我患了癌症,儿子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他很争气,考上了北京大学。

有人说,人一辈子最大的成长就是学会感恩。回首这10年,我庆幸能在北京遇到那位主治医生,没有他我不会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药能救我的命;我也特别庆幸能够找到与哈佛合作多年的盛诺一家,没有这样靠谱的转诊机构,我不会顺利地来美国治疗。美国医生不断给予我的鼓励和坚持,让我知道别放弃,绝境中仍然有希望。
这十年,艰辛、彷徨、痛苦、绝望,再到希望,想起来真是说不尽的五味杂陈。还记得在北京治疗时同病房的一位妈妈。她对我说,别老想着死啊死的,一定得活下去,要不孩子们还那么小,没了我们,不知道她们要受多少苦。那时,即使头发掉光了,疼的整夜睡不着,面对前来看望的5岁女儿,她还是会开心地笑、讲故事。可惜,这样的笑容她的女儿再也看不到了。假如当时她能知道,大洋彼岸还有另一条路,该有多好。

在美国治疗的4年里,我还明白了什么是“责任”。我永远记得美国医生的这句话:“虽然我不能保证治愈你,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你只需要把你的所有担心交给我,让我来担心,我会对你负责。”
我也把美国医生的这句话带回了国内,作为一个老师,我告诉每个学生的家长:“你们不要担心,虽然我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考上清华北大,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请你们把担心交给老师,应该由我来为你们操这个心。”
从美国医生身上,我开始知道,如果国内每个行业,每个人,都能真的发自内心的各司其职,尽自己的义务,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的进步,我们有限的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