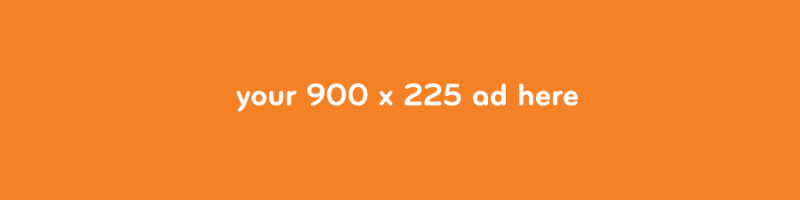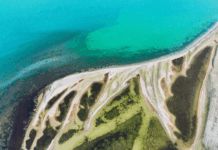芮效俭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需要进行一定调整,以反映现实的变化。这理应成为美中开展合作的领域,两国可以发挥各自作用,推动国际体系更加完善,使之更好地满足所有国家的诉求
1978年,我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当年7月起,我们开始同中方就美中建交进行秘密谈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公布后,我感觉到,这必然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变革。但这种转变会将这个国家带向何方,我心里却没有底。随后,中国开始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看清,改革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多么巨大的跨越。
作为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外国学者,我是幸运的。1938年,3岁的我随父母一起去中国。我的父亲后来成为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教授。我目睹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至今,我仍记得日军轰炸成都的场景。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我正生活在那座城市。再往后,我又亲身参与了美中建交过程,并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重回中国。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我见证了中国在上个世纪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因而也能更好理解中国的发展进程。
1979年,美国设立驻广州总领事馆。当时那里还没有国际化酒店。至今我还记得北京第一家国际化酒店——建国饭店在1982年建成时的场景。如今,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完全改变这个国家。放眼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面貌曾在如此短时间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自然是经济发展。前些年,我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敦煌。这座古老的小城如今已经接入高速公路网,还建起了现代化的机场。我再去武汉和成都时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已不同,每一处地方都有了明显进步。坐高铁去徐州时,我发现当地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先进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社会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开放。改革开放前,一个外国人要在街头问清时间是很困难的事。20世纪90年代,当我重新回到中国,开放而自由的交流无处不在。中国的发展使自身成为地区增长的动力源,给许多东亚经济体带来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今天,一些美国人在说,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了改变中国。然而,我认识的所有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美国的决定纯粹基于对美国利益的把握——中国“入世”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这也正是全球化带给美国的好处——比较优势理论不仅在国家内部起作用,也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这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
我儿时的玩伴都是中国人,父母的很多亲密朋友也是中国人。有些美国人尽管也为中国文化所吸引,却习惯于将中国视为“不同”。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的个人哲学理念是,美国政策不应损害任何一国民众改善生活的机会,各国有权实现自身发展。
如今,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后将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并宣称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人显然没有认真分析中国执行的政策。中国向来主张要维护现有国际体系,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完善。例如,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出发点就是要对现有国际秩序加以补充和完善。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需要进行一定调整,以反映现实的变化。这理应成为美中开展合作的领域,两国可以发挥各自作用,推动国际体系更加完善,使之更好地满足所有国家的诉求。
作为外交官,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和大国打交道——其中,9年时间与苏联打交道,其余多数时间是与中国打交道。我总结出经验,即所有大国关系必然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说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是非常有益的一种提法。面向未来,我们正需要一种新的哲学基础来思考美中关系。
(作者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前驻华大使,本报驻美国记者胡泽曦采访整理)
《人民日报》(2019年01月02日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