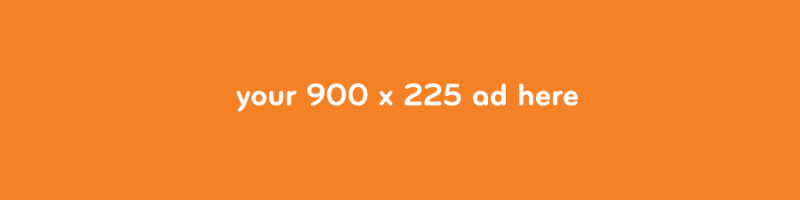小杜 独立文学创作者
陈焕生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四平八稳地被玉米地包着,随处可见开着“公羊”皮卡美国大叔,膀大腰圆,浑身晒得通红。商场里最贵的牌子也只是Polo或Coach。若非是最近丢了个中国学生,国内根本没人注意这里。
时日一久,国内的小留(学生)们也养出了一种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开两个小时高速去趟芝加哥,叫“进城”。品牌店扫通货,唐人街吃顿重庆火锅,大包小包开车回来,一路夕阳,玉米地绵延无边,便又“回村”了。
解馋扫货之类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却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
女小留还好,往长里留就是了。除非恋爱或考试受了重挫,咔嚓来个短的,不然都是留到回国,或焗或染,回村能顶大半个学期。可男小留就难办了——或者说家里没那么有钱的男小留,就难办了,比如陈焕生。
因此,大家频繁光顾的,也就韩国李大姐那家。
1
李大姐这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细小。当街挂个牌子,Lee’s Hair,再串俩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过,收了风铃,牌子就哑了,便是收工了。小留们虽频繁光顾她家,暗地却常笑这棒子英语忒烂,硬生生把一理发店起成了“李的毛发”。
老李家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Nasha、Dargo和老板李金姝。
只要康德姐出工,小留们就肯定排她的号,一是大家同是中国人,二是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只是专业不好,搞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认识了一老美,漂洋过海嫁来,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里呢?
康德姐嫁过来之后,还生个女儿,不折不扣的混血,浑身那漂亮劲儿就像小说里虚构出来的。
可惜,孩子出生没多久,老公就死了,车祸。细雨天,八十脉的高速,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翻。老公生前是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还处于还各种债的爬坡阶段。康德姐刚生完孩子,绿卡没排下来,英语也没讲利索,一夜之间就成了遗孀——欠着各种债的遗孀。
康德姐开始去教会,抱着女儿受洗,跟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了这段经历。英语虽磕磕绊绊,但还是有人当场听哭了,一些援助随之而来。
中国人一般直接出钱,匿名,塞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是实实在在的钞票。老美毕竟在自己家门口,花样就多了:有人帮她找律师摆脱各种债务,有人帮她申请各种政府救济,还有人建议她在教会幼儿园帮忙看小孩打零工。这其中就有位韩国大姐,李金姝。
李大姐最开始带来的是一罐罐辣白菜、一板板冷面和一盒盒烤海苔片。往来几次,李大姐问康德姐,你会不会剪头发。康德姐当时就哭了:丈夫出车祸那天,本是要去匹兹堡开会,西服衬衫是她洗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出事当天,剪掉的头发还在垃圾桶里,淡黄色一缕一缕,被康德姐捡出来,收在一个小盒里。
李大姐也听哭了,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店里,从零工做起,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康德姐也确实像样,一大早把孩子放教会幼儿园,上午在老李家打工,下午去镇里的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连哄再喂,伺候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的中餐馆端盘子。
如此熬过大半年,英语说得溜了,社区大学听说了她的情况,提前颁发了毕业证书,从此便正式在老李家出任理发师:15块美金剪个男发,李金姝抽9块,剩下6块加小费就全归康德姐。照这边的行规,已经没法再够意思了。
2
康德姐一出道,就受到小留们的热捧。
这自然先归功于她是中国人,讲中文,无论剪什么发式都能沟通。不像李金姝,虽然剪得卖力,但英语忒差,刷刷剪完,都一个模样。
跟康德姐就舒服多了,不但能用母语聊发型,还能聊哲学。康德姐给陈焕生说,她的专业虽是存在主义,研究加缪和萨特,但内心里还是喜欢古典主义哲学,最爱读康德。
话说康德,独居在德国的一个小村,生活简单,作息规律,村民们甚至以他的起居活动为钟点:康德起来散步了,大伙该种地了;康德中午回家读书了,大伙就吃午饭了;康德晚上出来遛狗了,大伙也收工了。
当然,她的顾客远不止陈焕生一个,她跟所有人都讲康德遛狗,用一口嘎嘣溜脆的京片子。很快就被起了外号“康德姐”。
大家私下里说她为了省趴车费,晴天骑单车,雨天坐公交,比天气预报还准,论其规律性,恐怕也不输康德多少。
康德姐剪起头发来奇快无比,一手捋头发,一手下剪,简直就是薅羊毛。这一点小留们也喜欢,因为大家不像老美,把理发当成享受。小留们都是用中午下课晚上吃饭的边角时间来排号,剪完赶紧走人。当然,小费就给得不大情愿,康德姐却表示理解,毕竟国内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她就更有理由剪得更糙更快了。好在双方都不在乎。
没多久,秋季入学的时候,康德姐竟单飞了。
她东挪西凑盘下主街对角一间小屋,自己当老板,店名起的也够哲学:“康德的钟”(Kant’s Clock),狠狠摆了韩国东家李金姝一道,因为这是每年争抢顾客的旺季,而李大姐新招来的Natalia还三心二意。
不仅如此,“康德的钟”还推出了新花样:剪一个头只需10美元,只排10分钟,比煮两包方便面还快还省。小留们自然都被吸引过去了。
陈焕生因为有点喜欢Natalia,就坚持留在了老李家,这是后话。
李大姐那英语依旧一股大酱汤味儿,头发依旧剪得一丝不苟。陈焕生耐着性子听她絮叨:“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不是不让她走,可打一声招呼就那么难?周日还在教会里一起唱赞美诗,周一就在街对面成仇家了?我给她女儿买了礼物,还要认干亲哩!”
讲着讲着,她突然停住,直起腰,晃一晃脖子,仰头长叹一口气,想来是一天到晚弯腰扭脖落下的职业病。舒展好身体,她口气也变了,还是从“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开始,说到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丈夫的车祸,又说到她那个天使一般漂亮的女儿,因肺炎烧成了哑巴。
陈焕生听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中国女人不知给他剪过多少回头,讲过多少回康德遛狗,他却从未听过这些。除了一个外号、一窄条削瘦的身形和一口京片子以外,他对她一无所知。
3
Nasha可不是外号,是Natalia的昵称。
她刚来老李家时也很瘦,一双大而深的蓝眼睛,本该让人联想到月亮或湖水之类的比喻,却因瘦而塌陷得太凶,让整个人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可惜这都是陈焕生一厢情愿的想像,人家可自得其乐:夏天穿条夸张的短裤,一条腿又白又直,另一条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刺青,绿得发了蓝。
暑假客少,一有空闲她就拉上康德姐抽烟,站在Lee’s Hair的风铃下,一黄一白两个中年女人都奇瘦无比,陈焕生过目难忘。
Natalia是白俄罗斯人。小留大多不知这小国的英文名,生搬硬造问,“So you are from White Russia(你是白色的俄罗斯人么)?”
Natalia就很生气,用带着东欧腔的英语反击:“My country is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We have damn nothing to do with stupid Russia(我的祖国是白俄罗斯,和傻逼俄罗斯没一毛钱关系)!”
Natalia不但脾气大,还对政治特敏感,疑心所有来这儿的中国人都是党员。陈焕生觉得好笑,就耐心解释国内如何选拔党员,还说他就算是党员,现在肯定也不是了,因为在美国连怎么交党费都不知道。
可Natalia早已失去耐心,嘟囔一声“Whatever(爱啥是啥)”,便扶着陈焕生斜躺在理发椅上,拧开龙头。
“热么?”她问。
“不热。”
“冷么?”
“也不冷。”
“您大概是一条蛇或者蜥蜴吧。”
Natalia爱把金发扎起来,盘成髻,刘海散开一小缕,弯腰给陈焕生洗头时便垂下来,扫到他脸上,被她一口吹开,他便实实在在感觉到了那种混合了香烟、咖啡和口香糖的奇异味道。那双蓝眼睛就在他上方,从未被这个角度凝视过,他慌得闭上眼,假装享受温水和她手指在他短发间抚过。剪发前洗五分钟,剪完后冲五分钟,每个月十来分钟的亲密,让他对这女人念念不忘。
陈焕生这专业读得不顺,换过两任导师,一个博士学位比别人多读三年。他多读了不少书,当然,都是些所谓没用的书。其中一类最无用,便是文学。
可每个月来老李家一次,竟让他发现书也很有用,因为Natalia雪白的膀子上纹了蓝色的大胡子老头儿,底下一行斜体字母,D开头。一问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陈焕生心下大喜,忙说自己喜爱俄语文学,通读过托尔斯泰全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很吃力,中译本都太拗口了。
岂知Natalia听了一撇嘴,高高吹起散开的刘海:“俄语?文学?Nie,nie,nie(不,不,不)!”
Natalia在读大三那年去了趟巴黎,连走亲戚带游玩,顺便在一家彻夜举办俄语文学沙龙的咖啡店打工,昼夜颠倒地泡在不加伴侣的黑咖啡和索尔仁尼琴之类的字眼里。
“那为什么来美国?”
“还能为什么?为了一个美国男人呗。搞文学评论的,光骂别人自己却写不出来那种。拿到绿卡我就跟那狗娘养的拜拜了。”
“对不起,Natalia。”斜躺在理发椅上的陈焕生睁开眼。
“对不起?得了吧你!叫我Nasha好了。”
Nasha,娜莎,让人心里麻酥酥的名字。陈焕生又闭上眼,感受着水温和她的手指
4
那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陈焕生以为机会来了,特意网购了英文版的《锌皮娃娃兵》,想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Nasha,没成想却惹得人家大发脾气:“把它拿开!收集别人苦痛,编成一本烂书,署上自己名,卖出去得奖,到底算哪路英雄好汉?算哪门狗屁文学?”
陈焕生很尴尬。电脑里整天放韩国偶像剧的李金姝在一旁听得更是一头雾水。
“好啦,陈,对不起。我离开那狗娘养的好几年,可一张嘴讲话还那么像他。”Nasha发完脾气就出去抽烟了。
偶尔赶上Nasha开心,会给陈焕生做上两分钟脖颈按摩。她手腕很细,又没什么汗毛,简直不像白人女生。陈焕生撑起胆,磕磕巴巴说出这话,Nasha听了大笑:“陈,你这傻瓜,不会连女用剃刀都没见过吧?你应该跟我老板去她们教会看看,听说有很多亚洲女孩,都是单身,你该找个女朋友啦!”
亚洲女孩?找个女朋友?这是拒绝么?陈焕生想约她出来,却一直没敢说出口。
偏偏Nasha又说些没心没肺的:“喂,陈,你猜今天有几个男的要我电话?才两个。昨晚我又没睡着,现在看起来肯定像坨屎,但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吧?这帮狗娘养的,因为我是个洗头发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笑话。你知道他们说我啥么?说我发音可爱!Fuck those American pigs(去他妈的美国猪)!”
不消说,这在他听来更是拒人千里了。

康德姐跑到街对面单干的时候,李金姝气得大病一场,Nasha一人在风铃底下抽烟。
“唉,那个中国女的是个真正的婊子。但谁又不是呢?生活本来就是个超级大婊子!”她背对着陈焕生,仰头吐了个烟圈。
康德姐走后,李金姝为多留顾客,不得不把Nasha从零工转成理发师。可到底不放心,因为Nasha说有几个白人男的总对她上下其手,还说再敢这样就用剪子戳瞎他们的狗眼。
陈焕生攒不够找Nasha洗剪吹的勇气,又舍不得离开,只好坐在李大姐的镜子前,任凭心上人那双蓝眼凝视着别人,对着别人怒骂诺贝尔奖,让别人也叫她Nasha。
终于鼓足勇气,他决定大大方方约她出来,独立日请她去密歇根湖畔看午夜烟花。成就成,不成以后就不想了。
当陈焕生带着必胜的兴奋和必死的悲壮站在风铃下,店里却只有李大姐一人忙乎。一问才知Nasha病了。等了一礼拜,Nasha还是不在,反倒是一个穿紧身T恤的大胡子在冲他笑。
“Natalia哪儿去了?她到底怎么了?”他问李大姐。
“她不干了。去别的州了。”
“别的州?为什么?”
“去能让她堕胎的州了。”
原来,他的Nasha前一阵发现自己怀孕,很是歇斯底里,没法相信自己三十好几,居然“还犯中学生犯的错误”。而这小镇恰好位于美国中西部“Christian Belt”,所谓“基督教地带”,堕胎有悖教义,更属违法。李大姐劝她生下来,说这小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哪怕是不请自来,教会肯定帮忙的。
Nasha撇撇嘴,标志性地一吹刘海:“如果耶稣能搞清是哪个狗娘养的把这礼物塞我肚子里的,把它生下来也无所谓。”
李金姝信主多年,又有一种大韩民国式的执拗,当下被这态度激恼了。两个女人用各自乡音浓重的英语大吵一架,Nasha愤然离开。临行前居然又跑过来,给老板一个满是大麻味道的拥抱:“李,我虽不信你那套,但你是个很棒的人。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跑掉,但再不抓紧跑,打胎钱就更掏不起啦。”
李金姝对陈焕生指着那个大胡子:“新来的Dargo,是我见过手艺最棒的,你要不要试试?我发誓再也不招女人了。”
剩下陈焕生茫然无措,不知该转身走掉,还是该躺在曾感受过水温和Nasha手指的斜椅上。
5
Dargo来自阿根廷,据说十几岁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混。手里握着一把沉甸甸的大剪刀,黑色的刀身,一般女理发师根本摆弄不了。剪柄末端连着一只金色的螃蟹,随手指动作连起一片金光。
问是不是纯金的,Dargo便憨呼呼笑了,露出一口健壮的白牙:“This is from my little bitch. Ask him.(我小婊子送给我的,问他去吧)”
小婊子,Dargo和Jimmy对彼此的称呼。
Dargo不抽烟,只喷古龙水,闲时只拾掇那把剪刀,擦得干干净净,收在刻有“D&J”字样的木盒里,然后去吹他的口琴。那口琴也是黑色,很小,让他大手一衬,活像块长条形巧克力。斜躺在理发椅上,凝神静气,口琴埋进络腮胡里,曲子就出来了。时而忧伤,时而欢快,从一团胡子里流出来,流遍整个店铺。
Dargo那柄大黑剪使得刷刷作响,不愧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攒下的功底。但男小留都抱怨说这厮盯着他们脖子的眼神不大对劲,女小留们则迷上了这位爱穿紧身T恤的南美汉子,尤其是他在Jimmy过25岁生日那天专门剪掉了胡子,露出那个“能夹住口琴”的肉乎乎的下巴。
不少姑娘找他合影,传到朋友圈,一来二去那柄螃蟹剪子就被排满了。
李金姝对此很满意,因为女生只要动动剪,喷一喷,蒸一会儿,就能消费上百美金;而男生只能收二十块,小费吝啬,还不守时。
于是,两家小店竟出现十分明显的“瓜分局面”:男小留纷纷去了“康德的钟”,女小留因Dargo都结伴逛老李家。
至于陈焕生,还是照旧。倒不是痴盼有一天Nasha突然回来,而是出于惯性。李金姝给他披上了银色的纱质围巾,Dargo的口琴声在旁边响起。
“我该给你这小调儿付钱么?”Nahsa走了,陈焕生不再紧绷绷的,也能开个玩笑。
“要付就付给我婊子,琴是他送的。”
说笑代替了琴声,李金姝在一旁皱起了眉。
Dargo的小婊子叫Jimmy,一个膀大腰圆一黑哥们,总会骑摩托来接他下班。一黑一褐两条大汉当街也不牵手也不亲吻,但跨上摩托之后,一个就紧紧搂住另一个腰。
不让Nasha打胎,然后招个南美的同志?陈焕生很想问李大姐你这教到底咋信的。但彼时,康德姐那边又招来两个中国人帮忙抢生意,他才明白若非Dargo给撑着,老李家早被挤垮了。
要说陈焕生和Dargo混得熟,还是在球场上。
这阿根廷人不知从哪儿拉来另一伙阿根廷人,七拼八凑一支球队,唧唧呱呱扎堆讲着西班牙语,每个人球衫背后都印着10号梅西,根本没人踢中后卫和门将,就拉陈焕生和Jimmy充数。结果队里梅西实在太多,对方连半场都过不来,Jimmy便倚着门柱和陈焕生闲聊起来。
原来,两人是在芝加哥的同志酒吧认识的。同居半年,Jimmy发现Dargo沉迷赌场,才坚持要搬到这小镇。当然,这是整部爱情故事的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Dargo觉得Jimmy住的黑人区毒贩太多,为了“小婊子”能读上博士才搬过来。
陈焕生听了还有点羡慕。
6
“晚上带你去‘蓝鸟’。别误会,开开眼而已。”散场的时候,Dargo和Jimmy笑嘻嘻发出邀请,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一个拍着另一个圆滚滚的屁股。
“蓝鸟”是镇上唯一的同志酒吧,晚十点开门,后半夜灯火通明,警笛跟狼似的在外面晃来晃去。陈焕生被保安拦住了:“请出示驾照(美国驾照相当于身份证)。”
Dargo冲他挤挤眼:“别怕,这只是确定你年龄,跟你是直是弯没关系。”
酒吧当中一个大舞池,男人们脱光膀子往里蹦。酒精,汗味,荷尔蒙,催命般的隐约,说是黏糊糊的肉池也不为过。只有陈焕生穿了件T恤。
一股大麻味扑鼻而来,有人凑上来搂他,被Jimmy一把推开:“Fuck off man! He is my bitch(滚,他是我婊子)!”
陈焕生浑身是汗,要了杯冰镇苏打水。灯光闪烁中,两个留着山羊胡的白人大叔在角落里热吻,大毛腿叠着大毛腿。他留下一张十美金的钞票,想独自离开,却被Jimmy拽住:“别走啊,好戏还没来呢。”
所谓好戏,便是Dargo与两个墨西哥人合奏卡洛斯桑塔纳的曲子。Dargo独自搞定口琴和吉他,活脱脱一个南美版的鲍勃迪伦。
“You see that bro? Ain’t my bitch a real bitch(看到了么?我的婊子像样吧)?”Jimmy一边拍手,一边晃着黑人特有的浑圆臀部。
本该是个令人心醉的夜晚,却毁于Dargo和墨西哥鼓手一个醉醺醺的吻。两人大吵了一架,Jimmy踹翻桌子,扬长而去。
“Sorry,that bitch is fucking too bitchy tonight(对不起,那婊子今晚太他妈婊子了)!”Dargo咬牙切齿骂道。
Jimmy在学校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探讨黑人群体的LGBT文化,乐得大呼小叫卖掉摩托,买了辆单排的小吉普,计划暑假和Dargo来个最牛逼的公路旅行:密歇根湖畔一路向南,穿越南北美洲大陆,一直开到伊瓜苏大瀑布。
车牌照左边,Dargo涂上“I am so gay that I cannot drive straight(我太弯了,没法直着开车)”。右边留给Jimmy,本想涂“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值钱)”,但觉着不够脾气,就先空着,准备想好再涂。
可没过多久,就出了事。一天晚上,右翼极端分子持抢横扫“蓝鸟”,Dargo连中数弹,当场身亡。
Dargo的照片如轰炸机一般出现在各种新闻上:下巴还是那般肉感,照片底下却标着“遇害人”的字样。连篇累牍的媒体虽大抵把握着悲天悯人的调子,但“男同”“偷渡”甚至“毒品”之类或明或暗的字眼,还是让人浮想联翩。
那些曾经趋之若鹜的女小留们听了纷纷乍舌:原来摆弄过自己脑袋的家伙,居然是这样的人。
政治系有不少学生认识Jimmy,群情激奋,组织示威游行。于是这个午后风和日丽,“反对歧视”“让仇恨滚蛋”“爱是一切”之类的标语塞满了整个小镇。
理发店窗外是满满一街五颜六色的肌肤,Dargo的巨幅画像在上面漂浮。装有螃蟹剪子的木盒还摆在那里,“D&J”的字样依旧刻在一起。
死人永远沉默。李金姝和陈焕生默默地注视着这支年轻又愤怒的队伍。
“看见Jimmy了么?”女老板问。
陈焕生摇了摇头,对着吼声雷动的窗外。
7
此后,陈焕生就不再去李金姝家了。
那时候他正博士毕业,工作却找得一筹莫展,连实习机会都捞不着,学生签证一到期就只能拎个学位净身回国。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那几根头发上。
他在网上注册了好几家中介,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全是广告。对着这些广告,他一次次投出简历,还做了表格备份:红色字体是被明确拒绝的,紫色是走到电话面试,绿色则代表当场面试。
表格已排到四百多行,绝大多数是黑的,沉默的黑,石沉大海的黑。少数是刺刀见血的红。廖若星辰的是紫色。绿色则根本没出现过。
他不敢去想自己到底投出多少份简历,每投一次就像在某家公司门口行了一次乞。也不是没想过回国,也听说国内发展好,似乎到处都在欢迎海归。但回去的又有不少想再出来:“咱们是没出道的小姐,回国一落地就是出台了,就不值钱了。”
可小姐也好,出台也罢,陈焕生不得不做回国的准备:他在美国拥有合法身份的光阴正一寸一寸短下去。公寓是租的,穷学生攒不下值钱物件,一股脑捐掉了事。
他唯一要准备的,实际上就是卖车。那辆二手丰田车是他来这小镇第一年花八千美金买的,最后一年四千块卖掉。极为庸常的车型,载着他风雨无阻,默默无闻,从未添过半点麻烦。如今缘分将尽,人能为车做的,不过是打个对折卖掉而已。
赶上毕业季卖车的太多,丰田车和主人一样无人问津。奖学金也断了,必须要直面每月按部就班的房租和生活费。陈焕生一边在售车广告上降价,一边当起了Uber司机。帮他撑过在美国最后时日的,竟是一门心思要贱卖出去的车。
为省掉四十美金的网费,他每天去校附近的星巴克投简历,手机里Uber软件一闪,马上出车。
最喜欢接的活自然是机场,两头有客能赚一百多。要飞走的,都是有了目标有了奔头的人。刚落地的,更是充满希望。唯有驾座上的他,没有着落,像是一头脱落了牙齿的独狼。
不光脱牙,还瘸了腿。
原本是一周踢三场的人,看着新生们在球场上挥汗狂奔,突然就丢了兴味。没心思自己做饭,沃尔玛的炸鸡和冷冻甜圈成盒成盒买,活该贪便宜,二话没说就胖了。对着星巴克厕所的镜子,把自己吓了一跳。
陈焕生转身就回家拎着鞋奔球场去了。散场后躺在人工草皮上,胸肺像着过一场火,才知道是伤了,不知撕裂的是韧带还是肌肉。
主街上的他一瘸一拐。有人在风铃下招手:“好久不见!你这是怎么了?”是李金姝,正往窗子上贴广告。凑上去一看,才知是店里招人的。
“我挺好,就是工作找的不顺。”
“快进来吧。”
陈焕生又走进这何其相识的小店:最显眼的仍是两面镜子,靠窗那面一直是老板李金姝在用,堆满了剪子、雾壶和发胶,靠墙那面曾是康德姐、Nasha和Dargo,现在就只空对着一张椅子。
正是放暑假,小留们或回国或游玩,没有顾客,也没有预约。李金姝要剪个免费的,他执意不肯,却被硬生生地拽到椅子上:“如果明天就有面试呢?你这样谁会要呢?”
银色的纱质围巾披在肩上,陈焕生不得不面对镜子里那张发横的脸。
“你工作找了多久?”李金姝用手指夹住他的头发,开始下剪了。
“半年。”
“知道我丈夫找了多久么?”
陈焕生在镜子里摇头。
“四年。”
8
李大姐的丈夫,确切说是前夫,失业前在芝加哥国立核能所作研究。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联邦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这个除了核裂变就一窍不通的韩国男人被扫地出门,不得不操着磕磕绊绊的英语四处面试,从加油站到快餐店,碰了四年的壁。
三口之家就全靠李金姝一个人,在密歇根大道上的理发馆里用一把剪子苦苦撑着。十点上工,八点收工,手腕和脖子像被抽掉筋一样。可更令人绝望的是,丈夫患上了抑郁症,整个人就放弃了,放弃找工作,放弃家务,放弃儿子的功课。只有体重直线上升:刚失业时一百五十磅,四年后二百二十磅。
“你根本想不到咱们亚洲人会胖成那样,堆在超市的电动车上——那种给残疾人或重度肥胖症患者专用的车子——在速冻食品区转来转去,这就是我的丈夫。”李金姝下剪依旧很慢,说得也平缓,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是丈夫离的婚,理由是她可以好好抚养孩子,他这边还能从政府领到救济金和食品券,满足自己对垃圾食品不可遏制的瘾。所以她才带着儿子来到这小镇,开了这小店。
“离婚前我是不信主的。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你什么也做不了。我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大胖子,我不想离开他,却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呢?”头发剪掉一圈,陈焕生在围巾里深吸一口气。
“我跟他的医师通过话,说他有在服药。去年每个月都回去看他。今年儿子说不想再回芝加哥了,就改成寄支票。”李金姝打开水龙头,“过来洗一下吧。”
他躺在斜椅上,闭上眼,感受着那水从凉变温。
“陈,你要的只是一份工作,不是一百份。你自己要是放弃了,那谁也帮不了。”李金姝直起腰,晃晃脖子,仰头长叹口气。那一套舒展身体的动作。
陈焕生点点头。顶着这款新剪的发式,他开车去了大峡谷,在北美的山河壮丽面前忘记拍照。回村甩卖掉车,单程票飞回了国。杭州一家私企,天又热,水土不服,自然而然就瘦了下来。
经人介绍认识个本地姑娘,很快发展到一起看房一起看午夜场。一天电影散场,手机收来一封邮件。看标题是美国那边的,心下一动。送姑娘回了家,掏出手机读了两遍,才确定没错,真是波士顿那家公司,过去屡投不中,如今新开职缺,问Dr. Chen有没有兴趣面试。
有没有兴趣?他把头转向窗外,杭州的夜色与灯火缝合得如此温柔。
本想一删了之。可回去冲完澡,对着空调凉快下来了,才打开电脑,调出那张备份表格,亮绿色的加粗体,在最末一行输入那职缺和公司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