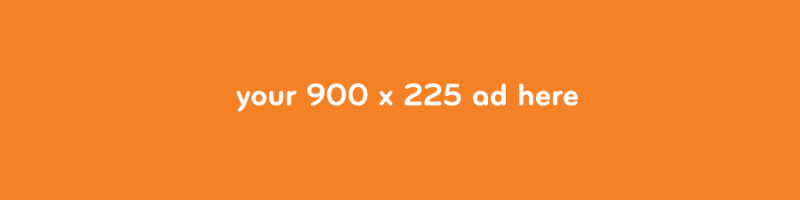Photo From The New Yorker
人们正似乎极为迫切地渴望自己的私生活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Facebook、Instagram、朋友圈甚至到“直播软件”。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直播自己的喜怒哀乐、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直播自己过马路、做爱…….
从Kim Kardashian到Paris Hilton,生活在红毯之上镁光灯之下的人们,一面极力掩盖自己的真实生活,一面又窃喜于风流韵事出现在花边小报的头条上。而屏幕后的我们,消费着、享用着这些信息,也“模仿”着他们。上世纪60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网络。
这篇文章将带你走近一个那个年代一个偷窥狂的生活,看他如何用一支笔和一个记事本写下三十年看见的一切——那个“曝光”,“隐私”这些词汇还很模糊的世界。

Gerald Foos 是个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1960年代,他在丹佛郊区买下了一个拥有21间客房的汽车旅馆——从此开始了寄居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偷窥生涯。
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在十多间客房的屋顶锯开长方形的空缺,装上假通风口,实则是他从屋顶窥视客房内一举一动的通道。他就这样躬身匍匐在倾斜的屋顶,记录着房内所见所闻,几十年来,竟从来没被发现过。
第一次认识Foos的时候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The reason for purchasing this motel was to satisfy my voyeuristic tendencies and compelling interest in all phases of how people conduct their lives, both socially and sexually. . . . I did this purely out of my unlimited curiosity about people and not as just a deranged voyeur.”
“购置这所旅店,既是为了满足我偷窥欲,也是为了我对人情世故的好奇——从性与社会的角度。所以,我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变态偷窥狂,更是一个对人类有无限好奇的探索者。”
我应邀来到丹佛。在机场刚落地,就看见他从行李带那边笑着走过来。Foos 已经四十多岁了,身形魁梧,留了一头利落的黑发,看起来像普通的酒店老板一样笑颜和蔼。为了自保,他要求我先签一份保密协定——未经过他允许,我不能泄露关于他的任何个人信息。
Foos 的父母是德裔美国人。“他们心地善良,愿意为我做任何事——除了讨论关于性的话题。”从小到大,Foos从未看见过父母做爱,或者对性爱有丝毫兴趣。父母的保守,反而激发了他对性的探索欲。早在九岁的时候,Foos就开始偷窥住在隔壁的姨妈Katheryn。Katheryn那时正是新婚少妇,身体像晨露中微湿的青笋一般蓬勃而香艳。她常常裸身在卧室里踱步,不拘小节地大开着窗帘,坐在床边摆弄瓷娃娃——Foos就这样躲在风车后注视着姨妈的胴体,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有时,他还会看到Katheryn和她的丈夫做爱。“我很嫉妒,我以为Katheryn应该是我的。”


图片来源《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Foos对Katheryn的痴迷之深,使他日复一日地偷看了六年。直到他长大在海军服役,Katheryn仍是他性幻想的对象。


在一本厚厚的笔记中,Foos毫厘不爽地记录了几十年来房间内每一对情侣或者夫妇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姓名、年龄、身材、家乡还有性行为。小小的汽车旅店,却收集了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足迹:趁午休和女秘书偷情的富商,结了婚或者同居的情侣,背着丈夫幽会的妻子,或者背着妻子偷腥的丈夫。到了70年代,他开始看到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三P、四P、群交、卖淫、招妓……
幸运的是,Foos的妻子多娜并没有因为他的偷窥癖而鄙弃他。相反,为了能够满足丈夫的需求,她卖掉了房产,转而随丈夫一起蜗居在汽车旅馆鄙陋的管理间。
“我很感激多娜。她没有因此远离我。也许这是她作为医务工作者的特质,在医院里她什么都见过了——生老病死,痛苦,畸形,疯癫,抑郁……结婚之前,我就和多娜坦白了。她爱我,她便接受我的一切。是她建议我用笔记录下我看到的东西。”
1966年,Foos在记事本中写下第一行:
“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梦想。我终于可以释放压抑了几十年的渴望和难以抑制的窥视欲。”
第一条:
Mr. and Mrs. W of southern Colorado
描述:35岁上下,男,白领,目测是差旅,5’10”, 180 磅, 大学毕业;妻子35岁上下,5’4″, 130磅, 丰满, 黑发,大学毕业,意大利裔,三围 37-28-37.
第一次偷窥房客,我心里非常紧张。观察对象都在我可视范围内。我第一次感觉如此有成就感,如此欣喜若狂——仿佛别人都臣服在我脚下,玩弄于股掌之间。
妻子洗完澡之后,开始在镜子里打量自己。她说自己开始长白头发了。男人开始抱怨在丹佛的工作。晚8:30,妻子脱光了衣服。她身材微丰,却非常性感。男人似乎没什么兴趣。后来两个人躺在床上,抽烟,看电视,亲吻,抚摸……男人很快勃起了,爬到妻子身上,两个人开始做爱。没有前戏。男人5分钟之后就高潮了。女人没有高潮,起床去洗手间清洗。
总结:这不是一个婚姻美满的夫妇。这个男人无知、冷漠,一心想着自己升官发财。他没有时间爱护自己的妻子。虽然空有个大学文凭,对性却显得无知而且冷淡。
第二条:
这对夫妇三十岁左右。说话三句不离钱,关了灯倒头就睡,睡得像死猪一样。
第三条:
十二月的一天。两男一女住进了一个单人间。
三个人中有一对夫妻,看起来友好且有教养;剩下的一个男人是红发。没过一会,三个人全都脱了个精光。红发男开始和女人做爱,女人的丈夫在一旁给他们拍照。
结束后,三个人都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开始讨论他们的吸尘器生意。


“I have seen most human emotions in all their humor and tragedy carried to completion. Sexually, I have witnessed, observed and studied the best first hand, unrehearsed, non-laboratory sex between couples, and most other conceivable sex deviations during these past 15 years.”
几年过去,Foos对自己的房客们越来越失望。人们的所作所为渐渐颠覆了他对这个社会原有的认知。所有的道德伦理、黑白是非,都开始在这些狭小的隔间里变得混沌、模糊,最后分崩离析。
“大多数人都在痛苦中度过旅行。他们为了钱争执不休……而只有在这个可怜的旅馆小房间里,他们才发现,原来两个人之间并没有爱。”
汽车旅馆的不远处有一个军队医疗中心,是当年越战伤兵的疗养院,所以旅馆内偶尔会有家属陪伤兵在这里过夜。一天晚上,Foos看到一个拖着假腿的伤兵和妻子住在楼上一间屋子里。
“为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干杯!”男人举起一罐可乐,对妻子说。
妻子抿嘴一笑,娇嗔地问道,“是…做爱么?”
“不!当然是钱!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你以为越战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那几个臭钱。”
几年之后,另一个伤兵和妻子住进了旅馆。妻子把瘫痪的丈夫从轮椅里扶起。两个人把行李包中的东西都掏了出来。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为什么还要爱我?”男人问道。
妻子深情地安慰他一阵,两个人开始做爱。他们都很享受,很投入——他们深爱着彼此。
还有一次,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衣冠精致的年轻男人来到这里。女人调了杯酒,脱掉衣服。两个人在床上云雨缠绵,女人正接近疯狂地呻吟时,男人突然停下来,说,“我最近要买台车,但是我付不起。”女人侧过身去,伸手掏出钱包,塞给他一张百元美钞。男人这才继续从后面进入她的身体。
满足了女人之后,男人还没有高潮。女人提出帮他射精,被他冷冷地拒绝了。“我还需要50块钱还债。”女人又塞给他一张钞票。几分钟之后,男人转身离去。
女人开车走后,Foos出于好奇,马上悄悄跟着她来到了她的住处——一个退休员工公寓。女人站在厨房窗边,满眼泪水。“后来我和周围邻居打听,才知道她是个寡妇,丈夫几年前死在越南的战场上。”Foos回忆道,“很多女人到了中年性欲正盛,而对于她来说,这是个彻底的悲剧。”
除了这几对情侣、夫妇,或者既不是情侣又不是夫妇,Foos更多的只是愈加的沉重和失望。他们百无聊赖地翻着电视节目,没完没了地谈钱、抽烟。他们把抓过肯德基的沾满油渍的手在床单上乱抹。他们不懂得性爱——男人只管动物交配一样的抽插,然后射精,然后倒头就睡;女人则一言不发地站起来,用床单擦干精液,然后倒头就睡。
他渐渐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偷窥狂——他俨然开始用上帝的角度去审视人类,开始失去对现实的掌控,开始沉入绝望和孤独。他曾以为,自己的“偷窥”实质上是一个严肃的,为社会福祉而贡献的科学实验。
“I’ve pondered on occasion that perhaps I don’t exist, only represent a product of the subjects’ dreams. No one would believe my accomplishments as a voyeur anyway, therefore, the dreamlike manifestation would explain my reality.”
他作出过这样一个数据总结:
1973年,在他所观察记录过的总计296次性行为中,有195次是白人异性恋,这些人最喜欢男上女下式;有184次男性达到高潮,而只有33次女性达到高潮。
次年,在总计329次性行为中:
— 12% 的男女性欲旺盛
— 62%的情侣或夫妇性生活频繁
— 22%性欲低下
— 3%几乎没有性生活


Foos 开始厌烦、嫌恶他的房客们——他们狡诈,欺骗,虚伪,失信。
“Society has taught us to lie, steal, and cheat, and deception is the paramount prerequisite in man’s makeup. . . . As my observation of people approaches the fifth year, I am beginning to become pessimistic as to the direction our society is heading, and feel myself becoming more depressed as I determine the futility of it all.”
他设计了一个“诚实游戏”。
在客房的衣柜里,Foos放了一个行李箱。当有房客登记入住的时候,他在房客附近假装小声告诉妻子多娜,“听说之前有个房客报警,他的行李箱落在我们某间房的衣柜里,里面有好几千的现金呢。”
房客们听到之后,故作镇定地走近自己的房间,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那个所谓的行李箱。这一切都被Foos 尽收眼底。找到箱子,房客们开始犹豫起来,是该撬开锁头,还是该把箱子还给旅馆。
在这15只“小白鼠”中,有市长、律师、军队上校…然而,只有两个人把箱子诚实地还了回来。余下所有人都想法设法撬开箱子,随后用各种手段销毁证据——其中包括那名市长。他索性把箱子丢进窗外的灌木丛里。

而他看到的不止是这些。
10号房住进来一对二十八九岁的青年男女。男人身形壮硕,大概有180磅上下。从偷听来零零碎碎的对话中,Foos 推断出他可能是个从大学辍学来的毒贩子;女人是金发,胸有差不多34D。两个人正值青春,性欲相当充沛——这让Foos非常满意。但是,使Foos 反感的是,10号房间时不时有人来敲门买毒品。他没有报警。一天下午,趁两个人不在,Foos偷偷潜入房间,把男人藏匿的所有毒品和大麻一股脑冲进了下水道里。
回房之后,男人发现毒品不见了,便怀疑是自己的女友偷走了这些毒品。日记中,Foos这样写道:“一阵争吵过后,两人开始付诸暴力。男人一把掐住女人的脖颈,掐得手臂上青筋暴起,直到女人断气而亡。男人不紧不慢,堂而皇之地收拾起东西,离开了旅馆。”
第二天,打扫房间的女佣发现了尸体,报了警。
直到今天,这场旅馆里的谋杀一直都没有破案。
我问 Foos, 你良心有愧么?
他这样对我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是我的错。我在这件事中的角色,和在所有房间里的角色是一样的:我是漂浮的,透明的,不存在且不干预的。反而,如果我报了警,警察盘问我是怎么知道藏毒的——事情会更糟糕。”
我一时语塞。
接下来的十余年里,Foos 还在房间里看到过自杀,看到过一个五百多磅的男人心脏斌突发猝死。因为他本来巨大的身体在死后变得更加臃肿,消防员不得不把他从窗户抬出去。


1999年,多娜逝世。
Foos卖掉了汽车旅馆,几年后与一名叫Anita的红发女人结了婚。
2013年,我和Foos再次相聚丹佛。距我们第一次见面已隔三载。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我和他都已鬓发斑白;而如今充斥着高科技、人工智能和数据的世界,看起来又是那么陌生,离奇且怪诞。
Foos有了一个新爱好:研究政府监控。
“人人都是偷窥狂,而世界上最大的偷窥狂就是政府。”科技、新媒体,让现在的人毫无隐私可言。他说,即使是中情局的局长都没法阻止自己的性生活成为报纸头条。政府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监视着我们的手机、短信、上网记录、信用卡、银行账户、GPS、航班号…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突然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我想是这样的。也许有一天,FBI就会来敲我的门,Gerald Foos, 我们有证据认为你这些年一直在偷窥他人,你是变态吗?这时候我会说,那你又是什么呢,Big Brother么?你是怎么知道的,还不是一直在偷窥我的生活?”
人生来即是偷窥狂。“男人热爱偷窥女人,女人渴望被偷窥。我猜这也是为什么男人看黄片,而女人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衣服首饰上。”他说。
但是,网络让偷窥变了味道。我想起了Erin Andrews,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曾经被人偷拍过洗浴后赤身裸体从浴室里出来并被发到网上。事发后,偷拍者被判为重罪,在监狱里服刑20个月之久。不仅如此,Andrews一纸状诉起诉了被偷拍时所在的酒店,酒店为此被处以5500万美金的罚款。
Foos对于此事的立场不出我所料。“虽然我说过,所有人生来都有偷窥癖,但有些偷窥者是为人所不齿的败类。他借助新科技,借助网络,把自己的观察对象放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是纯粹的暴力和恶毒的报复。这和我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我没曝光过任何一个人。如果我是陪审团,我也会认定这个人有罪。”
他认为,自己的偷窥和政府监视也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的偷窥是无害的,不为曝光或是伤害任何人。同时,他还觉得自己和斯诺登是一路人。“斯诺登是个揭露者——他揭露了政府见不得光的地方。而我是人性的揭露者,虽然我还没把人性见不得光的一面告诸世人。”


2014年,原来的Manor House旅馆被卖给了一家房地产商。几天之后,旅馆被爆破队炸成一片废墟。
“Seems that everything is gone.” Foos 说。
好像什么都没了。Foos打开车门,拄着拐棍,被Anita搀扶着,步履蹒跚地走向只剩下碎石乱瓦、断壁残垣的旅馆。
两个人流连了很长时间。最后,只找到一段旧电线和一块 Manor House霓虹灯牌的碎片。
“我们回家吧。”Anita说。
“好。”Foos说,“我看过的,已经太多了。”
原文作者/Gay Talese,编译北美留学生日报作者桥西。
原文来自The New Yorker: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04/11/gay-talese-the-voyeurs-motel